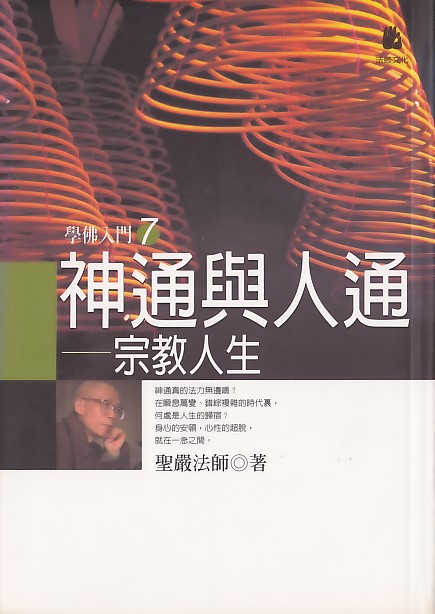
一、人生的現實面
我人生而為人,生而為生死不已而又無能解脫生死,無從得大自在的眾生之一,這一人生境界的存在,其本身的現象及其所能產生的種種思想言行,就是一大虛妄和一大缺陷。所以在我人歷史文化的演進上,在現實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組織上,隨時隨處,只要有著人類生存的所在,不論群居與獨處,人們都會存有一種「衝破現狀」的冒進意念,以及其從事於冒進的努力。雖然由於教育環境和個人修養(生活──人格知識的修養)的不同,其冒進的意念和冒進的努力,有著善、惡、美、醜、積極創造和消極頹廢(如不滿現狀或現實不能滿足他的要求而變成瘋癲,乃至自殺的人們)的種種差別,然而人們之想「衝破現狀」的基本觀念,卻是一樣的。可是不幸得很,人類自有生民以來,為了衝破現狀,為了爭取理想,經過了不知多少先民的努力,也不知努力了多少年代,時代雖然每在進步,現狀也在不斷演變,奈何人類的希望或理想,總是把人生的現實,遠遠拋在背後,使得生活於現實中的人們,永遠也追趕不上,像這種步步移動的人類歷史,和經常不能滿足要求的人生境界,豈不就是人類生存的一大悲哀!因為人生乃至一切萬物的存在,就是一大虛妄和一大缺陷,我人以虛妄不實的人生和缺陷處處的身心,去追求理想,創造理想,理想也就成了虛妄和缺陷,這種虛妄和缺陷的理想,即或有其完全變成事實的一天,但因它是虛妄而不是究竟,是缺陷而不是圓成,人類的生存,也就永遠站在各個歷史的立足點上,看理想之山的遠景,卻永遠是停留在「站在此山看彼山高」的現實之中,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是最後最高境界的實現,卻是一個不可知的無限期和無窮遠了!
由此可見,我人雖自覺實實在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生存在各自的現實之中,但是,試問︰我們的存在是存在於什麼之上或什麼之下呢?我們到底抓住了一些什麼東西作為人類努力的最終目標?即使他是大哲學家,也是無從解答,因為古人發明的真理,到現在已有些變成了不是最高的真理。那麼,我們看古人如此,後人之看我們,又何嘗不然?所以莊子要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正因為莊子的慧力,不能窮究宇宙界和人生界的一切事物而加以認識辨別和解答,所以他說「知也無涯」,以為用我人短短而極為有限的生命,要懂得一切的事物,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否則的話只有強不知以為知的病害而已。為什麼呢?因為莊子雖是中國思想史上一位傑出的大思想家,但他依舊還是一個人。所以莊子還有這樣的一段話︰「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磨,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這一段話說得非常哀痛,是一種不知生前,尤其是我人非死不可而又不知死後的哀痛!可知人生是一大虛妄一大缺陷,也是一大無知,請我們各自反問︰我對我們地球所處的太空世界的天文知識,懂了多少?恐怕即使你是當今權威的天文學家,也會覺得對於天體的知識,幼稚得非常可憐!我對我所生存的地球,認識了多少?對人類整個的歷史文化,知道了多少?對民族和國家,明白了多少?對社會環境,清楚了多少?對父母子女和親戚朋友,瞭解了多少?乃至我對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美德和罪惡,又覺察了多少?至於我人的生前和死後,自不必說了。單問這些,我們就可發現自己的所知,幾乎即等於無知了!所以聖人而如中國的孔子,還要「入太廟每事問」,以為「三人行必有我師」而主張「不恥下問」,正因自知無知,才能虛懷若谷地去「敏而好學」,可是,人總是人,所謂學到老學不了,人之學與不學,只是小無知與大無知,小缺陷與大缺陷之別,缺陷終究還是缺陷。
二、佛教的人生觀
然而,人生之可貴與人生之莊嚴,竟又全部表現在這一自知無知的自知缺陷,而來力求充實和彌補的精神之上,由此,人類的歷史才有進化,由漸次的進化而形成人類的文化和文明,例如筆者之能著手於這篇文字的寫作,也是出於這一缺陷的迫促,雖然筆者自己便是一個缺陷的存在。因為自知缺陷,而來力求彌補缺陷,總比不來彌補的好,不過有的人的彌補方法是自我安慰的自圓其說,好像掩耳盜鈴或鴕鳥的心理一樣,只要把耳朵塞起來,將腦袋悶下去,就覺得安全自在了(如西方的宗教徒)。有的人的彌補方法是以缺陷的本身去補充缺陷(如世間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學家)。有的人卻是叫人以擺脫缺陷而來彌補缺陷,實際上,也只有完全擺脫了缺陷,才是真正的沒有缺陷,因為人生就是一大缺陷,所以只有超出了生死界限,才有達到真正圓滿的希望,那麼,釋迦世尊說法四十餘年,就是說的教人超出人生生死界限的種種方法了。
同時,正因為佛教的思想,是叫我人超脫人生生死的大缺陷網或大虛妄海,所以就引起了許多思想家的非難和指責,以為佛教要人擺脫人生生死的現實狀態,而去追求一個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無疑是表明了佛教的人生觀,是厭世消極而逃避現實不敢面對現實的一種思想,例如近世的實驗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西元一八四二─一九一○)年,就曾這樣批評過佛教︰「佛家的涅槃,其實只不過免去了塵世的無窮冒險生活。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實只是一班懦夫,他們怕經驗,怕生活……他們聽見了多元的淑世主義,牙齒都打顫了,胸口的心也駭得冰冷了。」(《實驗主義》二九一─二九三頁)他又說出他自己的主張︰「我嗎?我是願意承認這個世界是真正危險的,是須要冒險的;我絕不退縮,我絕不說『我不幹了。』」(《實驗主義》二九六頁)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說是詹姆士的無知或武斷,只因為他是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人,他對於佛教的陌生,是因佛教的思想文化,在西方世界中的傳播,尚在萌芽期間。所以詹姆士的曲解佛教,我們不必訶責,我們只希望詹姆士的學生以及他們的同路人,本著探求真理的宗旨,對於佛教的思想來細心研究一番。比如佛教既然消極逃世,釋迦牟尼在成佛之後,為什麼不立即進入涅槃,而要苦口婆心,往返跋涉地說法度眾?佛教既然是厭世而又不敢面對現實和正視現實的,佛教中的諸佛菩薩,怎麼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心大願?這一悲心大願,又何止是一般所謂冒險的精神所能相比相望?因為佛教雖然主張出世,但其出世的方法,卻在入世,唯有入世最深,而且是作縱橫面的一往深入,才會穿過世間冒出世間的界限,而進入出世的境界。如果說世間是一個大球體,那麼佛教的出世,並不是我人站在一個空間的立足點上,單獨直升而像直升噴射機樣地向上飛騰,乃是叫人深入球體的每一個部分,穿透了球體,先能在球體之中做大活動和大開墾,而達到了遊刃有餘的程度之後,才是超出世間或人生生死的時候(請參閱〈人心的安頓和自性的超脫〉一文)。可見,我人要成佛,要得大自在、大解脫、大究竟、大圓滿──大實在和大滿足,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奈何,一般學人之不能對於佛教做深入的研究,只在表面上以各自的見解和心量來看佛教,曲解與誤解,實屬難免!即連一些自命為學佛修行的佛教徒們,也難免沒有這一可能。
三、救世的思想家
為了人類的現實問題,層出不窮地困擾著整個的人類生活,故在「衝破現狀」的意念之下,給我們人類的歷史,激出了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他們都能本著扶傾濟危、解困救厄的心意,為人類的病痛和人類社會的病態,開出了各自所以為對症下藥的方案。這一種心懷,站在人生求出路求落實的觀點上說,都是值得讚美,也值得慶幸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當今的社會情狀,能不能和其他類別的動物世界有些什麼兩樣或高尚,實在是個很大的問題!可是,歷史慢慢久遠了,思想家漸漸增多了,他們各自為人生開出的方案或出路,也跟著增多了。這些種種的方案和出路,擺在人類大眾的面前,正像將一大盤品質、色彩、大小、形狀各各不同的糖果擺在一群初初進入幼稚園的小朋友面前,琳瑯滿目,蔚為人類文化的壯觀鏡頭。使得絕大多數的人們,真不知道何去何從,看起來樣樣都有它的道理,好像每一粒糖,都會使得小朋友產生出來甜的感覺,即使是裹著糖衣的毒藥,然在沒有中毒死亡之前,根本辨別不出它會叫人中毒。為什麼呢?豈不是因了人類的無知?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孫中山先生主張「知難行易」,絕大多數的人們,確實如此,即使被歷史公認為先知先覺的人物,又何嘗超出了這一「不知所從」的心理現象,任便他們已為人生問題開出了若干個似是而非的出路,但有更多更多的問題,他們仍然覺得莫名其妙!因為人的本身就是一個大缺陷,要從大缺陷中覓取大滿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儘管擺在人類面前的是一個大無限的大缺陷,但是人類的意志,總是不會放棄了覓取一個大滿足的希望和努力,這也就是人類之所以能夠繁榮綿延而不亡族滅種的主要原因,因為大家都希望生存,且還要求生存得更安全更美滿和更有意義,憑著這一要求生存的意志,才造成了人類的世界和人類的歷史,所以中山先生的歷史觀,是著重在「生」的一個意義之上,而被稱為「唯生史觀」或「民生史觀」。可是不幸得很,在這一個要求生存而又要求滿足的情形之下,人類的文化固然在逐漸昇華了,同時人類的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了,因為「求滿足」的欲望,迫使人們發狂,引起一些喪心病狂者的搶劫侵略和奴役。直到目前為止,在每一個國家政府或社會體系之中,雖各有其法律制度,維護著各該單元中的每一分子的權益和安全。然而,放眼看去,如今國際社會的激烈競爭,豈不正在準備隨時拿出核子武器來,毀滅我們的人類世界嗎?這一戰爭的威脅,比起洪水猛獸對於我們原始祖先的威脅,豈不更為嚴重!更為可怕!
這一空前的威脅固然可怕,但其威脅的原始意識或原動力之產生的當初,又未嘗不是為了增進人類的幸福和拯救人類的苦難,比如共產主義之產生,在馬克斯的當時,因為他自己窮,受了窮困的壓迫,並且又同情西方世界產業革命後的勞工生活,工資之低,工作時間之長,工人生活之毫無保障,特別是童工的慘狀。馬克斯想要衝破這一不合理的現象,才產生了他的階級意識的共產思想,想不到他的這一思想,竟會引起了當代思潮的重大變化!又如基督教的產生,是因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為了要使他的民族脫離埃及的奴役,才假借一個叫作耶和華的民族保護神,作為民族運動的號召,而使流亡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民一致團結起來,逃出了埃及王的權力統治。這個出發點,未始不是可歌可泣的壯舉,然而他以宗教的迷信而大肆屠殺埃及的臣民(如《舊約.出埃及記》所載),卻是這一壯舉的反動了。及至耶穌出世,根據猶太教而創立基督教以後,耶穌本人,固為猶太教所迫害,而在基督教抬頭之後,竟又反過來數次狠狠地屠殺了猶太教徒。同信一個上帝,同是一個上帝(是基督教的說法)所創造的兒女,彼此殘殺,竟會如此之慘!
正因為大家都有缺陷,所以大家都想求滿足、求發展,而又不能溝通彼此的願望,共同協力,來向一個目標邁進,所以才有人與人間的紛爭,才無法求得一個永久的和平。人類世界的思想太多了,每一種思想都代表著一種渴望求其實踐(不一定就能實現)的主義,同時也可能潛在著一種給予人類的危機。人是一個缺陷,缺陷創出的缺陷,那麼缺陷的本身,就是一個危機──假如當在發覺危機尚未成熟之前,而不能予以及時改進或避免的話。譬如美國獨立之後而影響成功的法國大革命,是歐洲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壯舉,爭自由,爭平等,講博愛,可是因誤用自由平等,而死在自由平等之中的人又不知多少,有名的羅蘭夫人,便是因此犧牲而成名!餘如林肯解放黑奴,終死於黑人之手;甘地為印度獨立而努力了一輩子,臨了竟被他自己的同胞刺殺!因為有了缺陷的人,一方面想自求滿足,另一方面又不能發現一個或一樣足可滿足自己要求的人物,事實上也的確沒有一樣東西,能夠真正地來滿足任何人的所有要求。所以歷史上的聖賢,也不能沒有如此的遭遇,如佛教的釋迦世尊,他的法身固屬滿覺圓通的無漏境界,可是佛的人身仍為有漏,釋迦世尊會排泄如常人一樣的便溺,也會衰老死去,也會頭痛,也有人對他不滿與憤恨,而想加害於他;中國的孔子,他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在孫叔、武叔看來,孔子還不及他的學生子貢來得賢明;耶穌對基督教徒而言,是極為神聖崇高,但當耶穌受難遇害時,被行刑者置於兩個強盜中間,而且加於輕言戲笑與侮辱。
因此,任便世間代代有人歌頌完人聖人,和追求那些完人和聖人的境界,但是人人只能自許為嚮往聖賢的聖賢之徒,而不得自稱其本身就是聖賢。有人以為「聖域無止境」,因此而有儒家所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安慰話來。
如果要把現有的一切思想(包括宗教思想),擺在「圓成」或「圓滿」的天平秤上衡量一下,以照筆者的看法,除了佛教的思想能夠勝任之外,實在沒有一個撐得起來。雖然佛教的思想,在時代的眼光中,仍然需要做一番凝聚和開發的工作,亦如在佛滅之後約五百年的光景,印度之有龍樹(Nāgārjuna)、馬鳴(Aśvaghosa)及天親(Vasubandhu)、無著(Asaṇga)等之對於佛教思想的再肯定與再發明。但是佛教基本思想的穩固性質和究竟價值,是歷久常新的。佛教不必乞靈於任何的神祕和權力,仍能解答任何一切的問題,猶可圓融無礙,佛法是從佛的大覺智海之中流露出來,所以能夠圓融無礙,對宇宙界的自然現象,對人生界的倫理關係,不偏不廢,也不執不著。最大的發現是「緣生論」的物理觀和生命觀。一切的一切,在佛法的眼中看來,毫無神祕可言,無論什麼事物,只要它的因素夠了,便會形成它的結果,那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同時,佛教的最後境界是圓成,圓成的畢竟觀念,卻是無形無相而又如《圓覺經》所說︰「圓裹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的。實際上,我人也唯有完全放棄了現有的身心境界,和身心所處的境界,才是徹頭徹尾拋開了人生的缺陷,而邁入圓融無礙的境界。這一境界在人們粗看起來,似乎是逃世的。然而筆者在前面說過︰「唯有入世最深,而且是作縱橫面的一往深入,才會穿過世間冒出世間的界限,而進入出世的界境。」由此可見,為了真正的滿足,就不得不設法拋掉現實的缺陷,拋掉缺陷,便即拋掉人生,要拋掉人生,又不得不先來肯定了人生,深入人生而期通過人生,再超出人生。所以佛法的宗旨在教人出世,而出世的方法,則在教人更為積極地入世了。
四、東西方各說各話
佛教以外的其他思想,沒有一種是能夠徹上徹下圓通無礙的,不是出於武斷,便是訴諸神祕,最開通的思想也不能不有所存疑。其中除了如唯物思想之絕對武斷之外,還有一個共通的特性︰相信創造主或自然神的存在。西方的宗教家或基督教的經院派哲學家,固然相信有個上帝創造了萬物,也主宰著萬物。即使自古代希臘的蘇格拉底到今日英國的羅素為止,他們的心中,也各有各的上帝的觀念,雖然他們是泛神論或是接近於泛神論的有神論者。如泛神論的代表,斯賓諾莎的上帝,並不同於基督教的上帝之能生殺予奪,而是一個只能自愛和被愛的上帝,上帝既無法愛人,人也不可以愛上帝而希望上帝也應該來愛他作為報酬。泛神論者的上帝,是大自然的代表意義,因為他們識不透大自然的奧妙,自身又處在這個大自然之中,所以把大自然神格化了起來,又因為明明知道大自然的對於人類意志雖有阻礙之處,卻不會絕對主宰,尤其西方人的思想中(非基督教思想)以為人類是可以慢慢征服自然的(故有種種科學的努力和成就),人類前途的命運好壞,全看人類自己的努力改進與否而定。所以不能承認上帝有任何的權威作用。再說我們的中國,中國的孔子,是一位人文主義的大思想家,他除了人生社會的倫理問題,絕少談到人生以外的形而上學。所以孔子要「不語怪力亂神」,要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對於生前死後的問題,總是存而不論的。孔子雖主張「慎終追遠」,但其追思的意義並不代表他承認人死之後還有靈魂,只是給死者的恭敬及予生者的安慰。所以他對祭神的觀念也是「祀神如神在」的,而不是肯定真有神的存在。原因在他所以為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存疑觀點之上。可是孔子對於天與命的觀念,又特別重視,我們在《論語》中可以看到好些有關天命的記載,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又有單講到天字的,如孔子去見了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而子路不高興,孔子便發誓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又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與予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淵死,子卅︰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我們看了這些語句,可以明白,孔子的天與命,有點類似於西方哲學中的泛神觀念,孔子的思想,一方面積極努力人生的奮鬥,而不仰鬼神之助,另一方面孔子又因本身的無知(人生的缺陷),面對著宇宙和生命的無限,太多太多的問題,無法從他的知識經驗中得到答案,所以又不得不提出一個天和命的觀念,作為無可奈何的心理安慰,孔子以「天」「命」「仁」看同一體的數面,所以到了《中庸》上的一開頭,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既然說天命即是性,而人性本善,善即近仁,能仁便可盡性。那麼,儒家所講的天命或天道,就是宇宙萬物的本然或本體了,所謂「知命」,也只是知道順應著宇宙萬物的本然之本性,去生存活動罷了,說簡單一些,知命便是聽從我人的自性發展而去發展。可見這是近似泛神論的一種觀念,因為泛神論以為宇宙萬物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儒家則以為天是萬物的本性,人性是本性的一部分,同時也可將此一部分之人性,融入於整個的本性之中,這就叫作盡性。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哲學家和中國儒家的上帝,絕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雖然經過中古時代許多教士的努力,在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等的思想中借用了若干哲學理論,形成了基督教的神學,可是若將基督教的上帝拿來放在哲學的面前,就無法站得住腳了。
至於佛教,筆者於二年以前,也以為佛教是泛神論的,其實那是筆者的無知與武斷,佛教雖有近似泛神論之處,但卻竟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因在佛教的觀念中,宇宙萬物──諸法萬有,是平等自如,而又自如不動的,所謂法性法爾,佛陀不以為他的說法是創造,也不承認有任何東西可來創造什麼東西,這一點是不同於基督教的,所以稱無神;佛教不以為宇宙之中還有一個什麼真正本體的存在,也不以為我人僅是宇宙中的一部分,這是不同於泛神論的,故而仍屬無神。可是,泛神論以為我人可以化於無限的宇宙之中,也能成為無限;佛教的佛性,我人到達成佛之時,佛性也是遍滿一切,如來如去,無所不在的,這一點,又像泛神論了。佛性是人人都有的,成佛是個別成佛的,成佛之後,又是各各有其名號國土的,成佛是眾生各個自性的昇華,昇華之後,雖能融入法界的無限之中,仍可有其個別獨立的價值,這與泛神論者以為的一融入無限,便消失於無限之中,而不復再有個別獨立的價值可言,又不同了。可見佛教是近於泛神論而是無神論的。
在這裡,筆者希望順便說一說宗教間之神與神的分別,以資澄清一下我人對於神的觀念。粗看起來,無論是一神論或無神論的宗教,都有多神論的嫌疑。比如基督教是眾所周知的一神宗教,可是在基督教的觀念中,並不以為除了他們的上帝以外,不再有任何神明了,不過基督教以為除了他們的上帝之外,其他的神明都是惡魔罷了。再說佛教,不主張有個創造主或主宰神,所以是無神。然而,我們在佛經裡面,又可看到許許多多的神名神號,故而佛教徒絕不可說佛教是不講神的,其關鍵所在,只是佛教的神是三界之中眾生界裡的一種類別,不像基督教所說的創造神,同時也不如基督教所說的惡魔而已。佛教之中雖也有魔鬼的名稱,不過佛教的魔與鬼,絕不會如基督教所說的魔鬼那樣,永遠是魔鬼,永遠沒有轉變的機會,也將永遠要被上帝扔在煉獄中受苦。佛教所說的魔與鬼是有希望超昇,也有希望成佛的。佛教之偉大處,亦正在此,既不強調神祕的權威,也不敵視任何一個眾生。在此,筆者還要加以說明︰佛教的無神,絕不相同於中國史上如范縝、司馬光等所主張的無神,也不同於今日共產黨徒所說的無神。他們的無神,是不相信除了物理的自然行動之外,還有精神或靈魂的存在,佛教的無神,只是不承認宇宙萬物尚還有個創造主或主宰神的存在,所以此無神不是彼無神。
現在,我們可以檢討一下上面所說的幾種思想,究竟那種比較落實可靠?首先我們不要忘了,人生就是一大缺陷,從缺陷中開發出來的思想,雖也可以彌補一部分缺陷,但是缺陷之中,必然含有危險的成分。基督教的思想,乃是鴕鳥型的,為了困惱於現實的痛苦,便夢想一個上帝的天國,他們對於解除人類痛苦的意見,不是開發人生的價值或改善現實的社會,而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天國裡,以為受洗了的基督徒,死後可望逃避痛苦而進入天國。事實上,我們雖可不妨承認有個天國的存在,然而不靠自己的努力,單憑一次受洗而想得到上帝的赦罪和拯救,在理智上似乎是無法解答的,正如人之犯罪,不去將功贖罪,只憑人事關係,就可變成無罪,在制度上軌道的社會裡是不會產生的。如說那是一種信仰的精神安慰,那麼它與鴕鳥之將腦袋埋進土裡,就以為它的生命有了安全的想法,又有什麼不同!也許基督徒們對於這一判斷要提出抗議,他們總以為耶穌即是上帝的道成肉身,耶穌是究竟圓滿的人,不可能有缺陷,耶穌的話也不會有缺陷。那麼筆者希望抄錄一段耶穌死時的記載︰「釘他在十字架上……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祭司長和文士也這樣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耶穌大聲喊著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這段話見於《新約》的〈馬可〉及〈馬太〉兩福音中,我們看了以後,除對耶穌之被釘十字架而感到悲愴和同情之外,又可證明耶穌本人並非即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否則當其臨難之時怎會又叫上帝而且表示上帝已經離棄了他?可見耶穌其人並非毫無缺陷,如無缺陷,則其絕對不會對於遇難而感到恐懼。
西方正統的哲學思想──是指由古希臘沿革發展下來的哲學思想。我們談到西方文化思想,便很容易聯想到了科學問題,不過科學一詞,通常被哲學家們看成哲學的分門別類,所以科學是出自哲學的子體,哲學才是科學的母體,如談西方的哲學思想,自也包括了西方的科學思想。但是不幸得很,西方哲學主張人類可能征服自然,到達這一傾向的強弩之末,人類便開始物化了,人要利用萬物,人也被看成了萬物之一而來當作物件利用。如美國的現狀,他們忙著賺錢,也忙著花錢;他們在工作時固然緊張,在娛樂時也不例外,可以說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極其緊張和高壓的氣氛中度過來的,像這樣的生活情態,能夠維持多久而不發生血管爆破的中風絕症,實在很難想像!其中的危機,是在人類要以缺陷來補充缺陷,以缺陷的人類作為而想滿足缺陷的人類生活,越補越覺不滿,越不滿越感缺陷,到最後,就難免會像不會調琴的人把琴弦越調越緊,緊到不能再緊之時,弦線也就斷了!因此,到目前為止,已有許多西方人在嚮往東方人的生活情調了。
那麼,我們的東方,究竟又如何了呢?東方有兩股思想主流,一是中國儒家的,一是印度佛教的,在中國還有一股道家思想的旁流。(西周諸家的思想,除儒道二家之外,無大歷史的影響,故不談)
我們先說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對於中國人而成為中國人的造型上面,貢獻很大,尤其中華民族雖經幾千年的歷史,在內憂外患的消長變亂之中,仍然屹然立足於世界之上,儒家之功不可埋沒。可是儒家的思想,雖著重現實的人生,而開出積極進取的一面,奈因人類的本身就是個缺陷,儒家所開出的精神,自也不能沒有它的缺陷,便是因為受了知識範圍的束縛,只能教人應該積極進取,應該勇往直前,應該成仁取義,但卻不能進一步地說出為什麼要應該?應該了是如何?不去應該,又是怎樣?說得明白一些,儒家的思想是很現實的,但在這個現實的兩頭──生前與死後,來處與去路,卻無法得到交代。從大體上說,儒家的人生歸宿,是寄託在所謂「大我」──自己的、自己民族的,乃至整個人類的後代子孫身上。也就是希望把自己這個曾經存在的生命,向後代子孫身上去凝聚或團結。所以孔子要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所謂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孔子雖不想於在生之時去沽名釣譽,但在死後,卻以為如不稱名於後世,就不能算是一個君子。孔子為什麼會有這種思想?因為他的安慰處,就在這裡,如果連這點安慰也沒有,豈不覺得如此的人生太空虛也太無聊呢!孔子未能透過人生生死的界限,來替人生開出一條更為積極的路向,所以只能希望人做聖賢而不能進一步使人非做聖賢不可;不做聖賢而做小人,孔子只能說他朽木不可雕,卻無法指出成了朽木的人會有怎樣的後果?同時,孔子主張將安慰寄託於後代子孫的身上,中國人的腦海裡也因此而形成了一種並不太好的觀念︰把自己的財勢遺留給自己的兒孫,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因了自己所遺的財勢而安富尊榮;為了顧全其子子孫孫的生活問題,便不得不去想盡辦法,增長自己的財勢(這一思想在西方人的觀念中,並非沒有,但總沒有中國之甚且深)。可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秦始皇希望他的萬代子孫都做皇帝,然到二世胡亥,秦的統治就完了;還有其他的開國君主,往往於大功告成之後,大殺功臣以鞏固他們王朝的命運,但卻從未有過一個永不凋謝的王朝!其實,我是人,我的兒孫也該是人,那麼我能找到生活的依靠,我的兒孫豈不也有同樣的可能?如果兒孫皆靠祖上的遺產生活,我們的社會也就少了若干人的生產而多了若干人的消費,這種現象實在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所該有的,中國社會之不及西方國家,原因誠然很多,這一觀念之為害,似也正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能怪孔子嗎?孔子也是出自他的無可奈何啊!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則宜於大家族制的發展,這一自然形成的制度,又是基於倫理的觀念之上,儒家之倡五倫,對於中國社會的安定之功,實在很大,不過一到後來,由五倫而僅重父子一倫(也是片面的)之後,社會風氣也就失去了重心,於此可見,世間之學說,有其利必能成其弊了。再說中國思想的旁流──道家。道家的思想,在積極方面講,它給了中國人的一種生活的藝術,那就是教人養成一種怡然自得和隨遇而安的心境。近人錢穆先生說︰莊子的理想人生是要人各自約限於自己的分際之內,不必再有所嚮往。郭象(其對註解《莊子》的功勞很大)說得更好︰「茍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泰山不獨大其大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樁,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茍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失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叫人知足和滿足。叫人不要向外追求,只要朝內稟性,性滿性足雖小亦足,若性有所虧則雖大亦缺。這與儒家所說的「知命」,似有相通之處,使得人生的努力和理想,有個緩衝的餘地。可是道家在消極方面,給予中國人的遺毒,也著實不淺,如莊子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像這樣的態度,簡直是個鄉愿了。《莊子》上又有一段很美的文章︰「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卅︰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像這樣的人生境界,的確恬淡的可愛,可是,人之更可愛處,是在力求向上的意志,我們在這一段文字之中,卻找不出一點主動進取的意義。在這種思想的潛移默化之下,就養成了「得過且過」與「滿不在乎」的茍安心理和頹廢意識,如說莊子的思想也能給予人一種努力的目標的話,那該是他所說的至人或神人了︰「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但是,中國人的隱遁深山不問人世間事的思想,就從這裡來的,辟穀燒丹和養氣長生的古怪行為與古怪風尚,也是來自這裡。事實上,這是莊子的一個理想境界而已,莊子希望人能「合天德」「守天全」,之後可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可是,莊子的理想儘管好,而莊子本人,卻並不就是到了這一境界的人,他說真人是「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的,然當他喪妻之時,竟又哀感而無法自制了。可見莊子還是一個活潑生動的凡人,而不是他所說的神人或真人了。莊子既然是人,人就不能沒有缺陷,所以我們對於莊子的看法,除了同情他的可愛處,卻不必痛斥他的消極點,這是人生共通的憂患啊!
道家的另一思想──老子給予中國人的消極心理,也很不淺,比如老子根據「物極必反」和「否極泰來」的原則,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主張︰「曲則全,枉則直,漥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老子總以物理的眼光看宇宙萬物之生滅變幻,總以為物壯則老,老則衰,衰則敗,敗之極又復為生而壯而老。所以叫人要守物勢相反的一端,待機而取,因而近人錢穆先生要說老子是個精於打算的機會主義者。可是老子服膺他自己的思想,也許能夠做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地步,一般的人卻不能了,卻只知守於劣勢的現狀下,等待優勢機會的來臨,而不知憑其自己的力量去迎接機會和開發機會了。這對中國人的創造意識,實在是個很大的洩氣洞。尤其老子只看到了物理循迴的原則,卻沒有認識精神動向的特質,因為物理界的現象,固屬生住異滅、滅生住異地交錯流轉不已,精神則並不盡然,精神可以有週期的變動,也可以有一直向上的昇華,而且只有一直向上而達於無極無限的圓成大覺,才是人類精神的最大特性和可貴之處。我們舉個很淺的例子,人漸漸老了,生理各部的機能,也漸漸衰弱,漸漸不堪負荷了,這是證明物壯則老的原則沒有錯,可是有些人的思想,卻不會因為人的衰老而衰老的,相反地,多數的大思想家,越到他們的晚年,他們的思想則越發成熟,對於人類的貢獻也越加偉大。
人之有老死,不是精神的老死,乃是物體生理的衰敗,精神(在佛教稱為識或如來藏)雖因生理的衰敗而離開軀體,但是軀體之死並非即是精神之死,以照佛教的觀念,人死之後,人的精神仍然有其應有的歸依或投靠。不過這些道理,絕對不是老子的思想所能明白。所以我們只能討論老子的缺陷,卻不必臭罵老子的缺陷。
五、小結
以上所舉各種思想的缺陷,並非筆者對於那些思想的攻擊,而是藉此證明人生的缺陷,由缺陷的人生開發出來的思想,也就不能沒有缺陷。就以佛教來說,佛陀的境界當然不會有缺陷,由佛陀的境界,用嘴巴說出來成了語文名相,因為世間的語文名相,是由人起,人有缺陷,人類的語文名相就有缺陷,以有了缺陷的語文名相來表達佛陀的境界,所表達的東西也就不能沒有一些缺陷了。因有這個緣故,東方人雖多信佛,信佛者又不能沒有弊病,因為各人心中所有對於佛的印象和憧憬,絕對不是真正佛陀的境界,佛的境界,只有佛與佛間,才能知道,我人知道的佛,只是一種幻象而已!我人本著佛的種種言教去信佛學佛,也只是一些方便法門罷了。
但是我們應該明白,佛教之不同於其他的思想而又超出於其他的思想之上者,正是因為佛教的思想,能夠直下承當,和當下指明世法之虛妄不實;更可承認,如佛法而著於世法之中,佛法也是虛妄不實。(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於新店,刊於《海潮音》雜誌四○卷一及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