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為什麼要有戒律
有關戒律的概念,我們已在上一章講過了,有關戒律的脈絡,便是本章的主題。因為,凡是一種學問及其所賦的使命,唯有從它的來龍去脈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它的精神,可以確定它的未來的展望。
俗話說:「鋼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國家的法律,對於守法的公民,根本是不起作用的。但要維護守法者的安全和利益,又不得不有法律的設置,因為社會之中及人類之間的害群之馬,並非絕對的沒有。同時守法與犯法的善惡界線,也僅在於一念的相差,為了警策大家,不要闖過這一十字路口的紅燈,所以要有法律;為了保護大家,不因一念之差而造成千古之恨,所以要有法律。
佛教之有戒律,也是如此。佛陀成道以後的最初數年之中,根本沒有戒律,因為初期的佛弟子們,都以好心出家,他們的根器也特別深厚,往往聽到佛陀的開示以後,即使僅是三言兩語的點化,便會立即證入聖位聖果。小乘初果斷邪淫,三果斷一切淫;初果耕地,蟲離四寸,至於偷盜和妄語,當然不會再有。所以佛時初期的僧團,用不著制定戒律來約束大家,大家也就本來清淨的。直到佛陀成道以後的第五年,才有比丘由於俗家母親的逼迫,與其原來的太太犯了淫戒。佛教的戒律,也就從此陸續制定起來。這是為了維護僧團的清淨莊嚴,也是為了保護比丘們的戒體不失。
雖然,佛教的戒律很多,但皆不離五戒的基本原則,一切戒都由五戒中分支開出,一切戒的目的,也都為了保護五戒的清淨。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道德,也是倫理的基本德目,五戒的究竟處,卻又是了生脫死的正因。我們學佛的宗旨,是在了生脫死,五戒而能持得絕對清淨,離佛國的淨土,也就不遠了;因為比丘戒是通向涅槃的橋樑,比丘戒卻又是由五戒昇華的境界。
戒的功能是在斷絕生死道中的業緣業因。如說:「欲知過去世,今世受的是,欲知未來世,今世作的是。」要是我們不造生死之因,即使不想離開生死,生死之中也不會找到我們的踪跡了。
所以戒律的制度,不是佛陀對於佛弟子們的一種束縛,實是佛子的解脫道,也是僧團的防腐劑。佛子若無戒律作為生活規範的依準,了生脫死是不容易的;僧團如無戒律作為統攝教化的綱領,佛教的狀態,不唯一盤散沙,也將烏煙瘴氣!
因此,佛在臨將入滅之時,示意後世的佛子,應當以戒為師。正像一個國家,元首可以死,死了一個元首,再選第二、第三,乃至一百、一千個元首。只要國家的憲法存在,大家依法而行,這一國家的政制政體,也將不動不搖,並且達於永久。佛教只要戒律存在,佛教的弟子及其僧團的本質,也必能夠與世長存了。
第二節戒律的傳流
所謂「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凡是一種約束性的規定,雖然多能使人按步向上,但是這一向上而至最上的境界,即使人人嚮往,卻也未必真的能使人人皆去拾級而上,因為向上走去,固有一個可愛的境界正在等待人間的每一個人,然在未曾到達之先,首先必須付出登高攀爬的代價,這一代價是非常辛苦艱難的。再看一個滑雪的人,從高處向下,直溜急滑,該是多麼的輕鬆呀!所以登高向上,雖有美麗的遠景,卻要吃苦在先;下溜滑落,雖有隕命的危險,當下畢竟是輕鬆的。
因此,當佛滅度之後,佛弟子中,就有一個愚癡的比丘跋難陀,感到非常高興。他說:「那個老頭子去得正好,他在世時,規定我們這樣必須做,那樣不准做。如今他去了,我們可以自由了。」(《長阿含經‧遊行經》,《大正藏》一.二八頁下)這話傳到迦葉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悲痛。他想:如果真的如此,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豈不因了佛陀的入滅而隨著結束了嗎?同時,佛在入滅之際的最後說法,一開頭就說:「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遺教經》,《大正藏》一二.一一一○頁下)於是決心召集當時的大弟子們,編集律藏。
那是釋迦世尊入滅以後的第一個結夏安居,也是在七葉窟舉行的第一次經律的結集;參加的人數,據說是整整的五百位,都是大阿羅漢。當阿難尊者誦完經藏之後,即由優波離尊者誦出律藏,由大眾印證通過之後,最初的律部便告完成。但在那時的結集,似乎尚沒有做成文字的記錄,只是統一由口誦心記而已。
就這樣傳流下來,因為佛教散佈的範圍擴大了,印度的種族和語言又是非常的複雜,同時最遺憾的是,當佛滅度後,由於部分的長老比丘,並沒有受到摩訶迦葉的邀請,所以也沒參加七葉窟的第一次結集;從此以後的佛教,雖在長老比丘們的領導之下,過著與佛在世時相差不多的僧團生活,但已經失去了領導的中心,未能產生一個統一的,如共和政府式的機構,而僅能各化一方,各自為政。時間長了,由於地理環境的不同,由於彼此之間的隔閡,大家對於佛陀的教義,也就產生了若干不同的見解。這種不同的見解,便造成了部派分張的結果,那是佛滅之後一百年至三、四百年間的事。佛滅百年後在吠舍離的第二次結集,就是部派分張顯明的開始。所以,對於戒律的傳流,也由於部派的分裂,而成了部派的戒律,各部有各部自己所傳的戒律,至於初次結集的律藏,現在已無從見到它的本來面目,不過,現在所傳的各部律藏,無論南傳錫蘭巴利文系的《善見律毘婆沙》(又稱《善見律》)也好,北傳譯成藏文的有部律及漢文系的四部廣律也好,雖然各有若干小節的取捨與詳略的出入,但其根本精神及其根本原則,仍是大體一致的。所以律藏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並且也被近世學者,公認為最能保留原始佛教真面目的聖典之一。即使這些律部的分別出現,已是佛滅百年之後的事了。
據向來的傳說,律藏初次結集之後,即由迦葉尊者傳阿難尊者,再傳末田地、舍那波提、優婆崛多等五傳,在優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於各自對於律藏內容的取捨不同,律藏便分成了五部:
曇無德部──《四分律》。
薩婆多部──《十誦律》。
迦葉遺部──《解脫戒本經》。
彌沙塞部──《五分律》。
婆粗富羅部──(未傳)。
五部分派說,是根據《大方等大集經》卷二二〈虛空目分‧初聲聞品〉而來,但在該經之中,雖標五部,卻是說了六部的名目,第六部是摩訶僧祇部。(《大正藏》一三.一五九頁上─中)。據傳說,這是佛陀預記的事,佛陀早就料到律藏的傳承會分派的,這在《舍利弗問經》中,也有類似預記的記載而分為八派(《大正藏》二四.九○○頁下)。但據史實的考覈,部派佛教的分張,在佛滅後百年至三百年期間,可謂盛極一時,由上座部與大眾部的根本派別之下,又各分出許多部派,一般的傳說大約分有十八部,本末合起計算,則有二十部之多。現在綜合南北傳所傳的資料,所謂十八部,未必真有那十八部的全部史實,也未必僅有十八部,因為部派之下又分部派,分了再分,到最後,有些部派的隸屬系統,現在竟已無從查明;比如北道派,就是這樣的例子。據《大智度論》卷六三說,當時教團分為五百部(《大正藏》二五.五○三頁下),這也未必是事實。然據近人的研究,部派佛教的名目,多到約有四十多種(見《海潮音》四五卷一、二月合刊)。照理說,每一個部派均有各自應誦的律本,但從事實上看,能有律本傳誦的卻很少。有律本譯成漢文的,只有五個部派,現在且將之分系列表如下:

因為《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同樣出於薩婆多部,所以有人說應是《十誦律》的別譯(如太虛大師),也有人說是新薩婆多部,唯其與《十誦律》同部而所傳時地不同,當無疑問;又因飲光部只譯出戒本而未譯出廣律,所以,雖有六部,在中國通稱為四律。四律與五論齊名:《毘尼母論》(即《毘尼母經》)、《摩得勒伽論》(即《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此二論是宗本新薩婆多部律而解釋的,《善見論》(即《善見律毘婆沙》,這是解釋《四分律》的)、《薩婆多論》(即《薩婆多毘尼毘婆沙》,這是解釋《十誦律》的)、《明了論》(這是上座部系犢子部下正量部的佛陀多羅阿那含法師,依據正量部律所造,它的本律中國未傳),合稱為漢文律藏的四律五論。正因如此,在現行的世界佛教中,漢文系的律藏也是最豐富的一系。
從上表看出,上座部佔了絕大多數,大眾部僅僅一部律而已(《摩訶僧祇律》又稱《僧祇律》,應屬大眾部),事實上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大眾部的發展,雖然引出了大乘佛教,大眾部的典集──律與論,所傳的卻是太少了。
第三節律部傳來中國的歷史
中國之有戒律,始於三國時代,曹魏廢帝嘉平二年(西元二五○年),由中天竺曇摩迦羅,在洛陽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
其餘律部譯出的時間如下:
《十誦律》──姚秦弘始六年至八年(西元四○四─四○六年),由鳩摩羅什法師譯出,共五十八卷,又由卑摩羅叉改為六十一卷。
《四分律》──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西元四一○─四一三年),由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出,共六十卷。
《僧祇律》──東晉義熙十四年(西元四一八年),由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出,共四十卷。
《五分律》──劉宋景平元年(西元四二三年),由佛陀什共智勝譯出,共三十卷。
《解脫戒本經》──元魏時,由般若流支譯出,共一卷,其時約在西元五三八至五四四年之間。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唐朝武則天久視元年至睿宗景雲二年(西元七○○─七一一年)之間,由義淨三藏譯出,共十八種,一百九十八卷。
以其譯出的地點及盛行的時間上說,《十誦律》雖是姚秦時在關中(陝西)譯出,到六朝時則盛行於長江下游的地區;《四分律》的譯出地點也在關中,它的譯出時間比《十誦律》只遲了七年,但到隋朝才有人弘揚,到了唐初才由道宣律師的大力弘揚,而成為中國律宗的唯一法脈;《僧祇律》的譯出時間,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它是在建康(南京)的道場寺譯成,六朝時在北方稍有弘揚;《五分律》比《僧祇律》又晚出了五年,它在建業(也是南京)龍光寺譯出之後,則殊少有人弘揚;《解脫戒本經》比《五分律》晚出了一百多年,它的內容與《十誦律戒本》相同,故也無可為說;《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又稱《有部律》)的譯出,比《五分律》遲了將近三百年,正好是在南山道宣律師(隋文帝開皇十六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西元五九六─六六七年)以後的四、五十年之間,當時的律宗,正是《四分律》的鼎盛時期,所以義淨三藏,雖然遍精《有部律》,奈何孤掌難鳴。依照律的內容而言,《有部律》為最多,也最豐富,可惜直到現在,還不曾有人繼起為之弘揚過哩!
第四節戒律在中國的弘揚
佛陀的教法是平均發展的,戒、定、慧的三無漏學,就是這一平均發展的基礎,也是這一平均發展的中心工作,如鼎三足,缺一不可。但在佛陀的弟子,即使是佛陀當時的弟子,對這平均發展的工作,就不能勝任了;所以諸大弟子,各有所長,各成第一。但是,戒律又是三學的基礎,不持戒,解脫道的嚮往,便成妄想;所以戒是任何一個弟子都要持的,不過研究的心得是有深淺的,故以優波離尊者為持戒第一。
正因這一趨勢,到了中國,就有不學戒的比丘出現,並將學戒的比丘,特別立為「律宗」的名目,這是中國佛教的不幸!
上面說過,中國之有戒律,早在三國時代,中國之有中國的比丘,也在三國時代。當時由於《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的譯出,即請梵僧,立羯磨法,傳授比丘戒。但因戒經大部分未到,故也無從弘揚,直到《十誦律》譯出後約五十年後的劉宋時代,才有人弘揚;在宋齊之際,也有人弘揚《僧祇律》;一到隋唐以後,由於《四分律》的勢力抬頭,而達於登峯造極之時,中國境內也就只有《四分律》一部,獨樹其幟了。
《四分律》在中國的弘揚,是起於元魏孝文帝時的北臺法聰律師,以下有道覆、慧光;慧光的弟子有道雲、道暉;道暉的弟子有洪理、曇隱;道雲及道暉的弟子洪遵;與曇隱並稱的有道樂;道樂的弟子法上;法上的弟子法願。再有道雲的弟子道洪;道洪之下有智首;智首之下道世、道宣、慧滿。這些大德,人人皆著有律疏或律鈔。到了道宣律師,《四分律》的弘揚,便到了登峯造極;道宣律師對於律書著述的成就,也已到了空前的階段。他以化教與制教,別攝一代時教,又以三教判攝化教;以性空(攝一切小乘法)、相空(攝一切淺教大乘)、唯識圓教(攝一切深教大乘),三教攝盡大小乘法;又於制教分為三宗:實法宗(依薩婆多部明受──戒體為色法)、假名宗(曇無德部依《成實論》明受──戒體為非色非心)、圓教宗(道宣律師自明受──戒體為識藏熏種)。以道宣律師佛學大通家的資具,又以他唯識學的態度,精治《四分律》,融通大小乘,以為四分律義,通於大乘佛法。因為曾有這樣一位思想卓越,行持謹嚴,著述豐富的偉大律師,弘揚了《四分律》的精義,從此也就奠定了中國律統的基礎,那就是《四分律》的一脈相傳。但據靈芝元照律師(西元一○四八─一一一六年)的意見,道宣律師已是第九祖了,他們的系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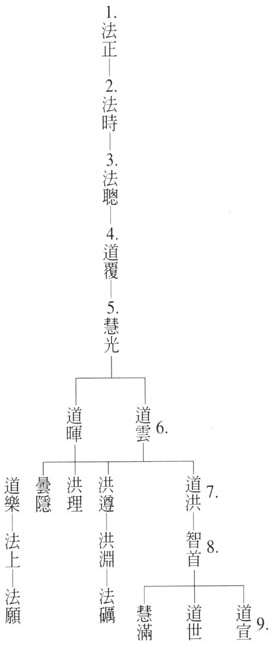
這一表系,是根據近人續明法師《戒學述要》的資料所列,但他們的系統,未必就是如此的呆板,比如《唐高僧傳》卷二一「慧光傳」中,將洪理與道雲、道暉並稱:「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大正藏》五○.六○八頁上);又於同卷「曇隱傳」中稱曇隱:「遂為(惠)光部之大弟子也」;又說到洪理著鈔兩卷:「後為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大正藏》五○.六○八頁下)這些都是他們在系統上錯綜複雜的關係。道樂的名字,見於「曇隱傳」的附錄,只說:「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又說:「故鄴中語卅:『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大正藏》五○.六○八頁下)至於道樂是出自何人門下,僧傳未有明載。上面列表,僅是大概而已。
《四分律》,在道宣律師的同時,共有三派,那就是:
南山道宣。
相部法礪。
東塔懷素。
法礪律師,出於洪淵的門下,道宣曾求學於法礪的門下,懷素則曾求學於法礪及道宣的門下,但因他們的見解不同,所以分為三派。他們主要不同處是根據問題:
道宣依於大乘的唯識。
法礪依於小乘的成實。
懷素依於小乘的俱舍。
他們三派,各有很多的弟子,也各有很多的著述,但以南山一宗最極殊勝,尤其南山律,通於大小乘,特別受到大乘根器的中國人所歡迎,所以歷久不衰,降至南宋,才算告一段落。
道宣律師有名的弟子,有:大慈、文綱、名恪、周秀、靈崿、融濟,及新羅的智仁等。弘景、道岸、懷素,也是道宣的受戒弟子。
文綱的弟子有道岸、准南等。
道岸的弟子有行超、玄儼等。
但在律統的系列上,是以周秀為南山的第二祖,他們的系統是這樣的:
周秀以下有道恆─省躬─慧正─玄暢─元表─守言─元解─法榮─處恆─擇悟─允堪─擇其─元照─智交(或立道標)─准一─法政─法久─妙蓮─行居等,共為二十一祖。再往以下,就入元朝,律宗衰廢,傳承不明了。
這是南山律宗的一脈相傳,到元解之後,即入宋代;到元照之際,已是南宋時期了。自道宣以下,解南山律者,共有六十餘家,撰述達數千卷之多,其中以錢塘靈芝寺的元照律師,最為大盛。但是南山一宗傳到靈芝元照時,又分成兩派了:
錢塘昭慶寺的允堪。
錢塘靈芝寺的元照。
這兩派,以靈芝的影響最大。
到了元代蒙人入主中國以後,中國的佛教,已經到了強弩之末的時期,律宗更是寂寞得可憐了;通《四分律》的,可記者僅是京城大普慶寺的法聞而已。同時由於南宋以後的禪宗,曾經一度盛行,故對唐宋之間的諸家律學撰述,既然無人問津,也就散失殆盡。
到了明朝末葉,弘律的大德,又相繼而起,比如蓮池、蕅益、弘贊、元賢等,均有律學的著述存世;約與蓮池大師同時的,另有如馨古心律師,專弘戒法,如馨的門下有性相、永海、寂光、澄芳、性祇等;在寂光(三昧)律師以下,著名的弟子有香雪及見月(讀體)二人。
但自香雪及見月之後,清朝二百幾十年,律宗的門庭,除了徒有其表的傳戒燒疤、跪拜起立等形式之外,已經沒有真正弘律的人了!晚近則有弘一、慈舟兩位大師弘律而已!(燒疤是晚近中國佛教的陋習,與受戒根本沒有關係,請注意!)
事實上,自南宋之後,由於律書的散失不見,明末諸大德雖想弘律,仍是續接不上古德的典型或氣運,更加說不上媲美於唐宋的成就了。說來,我們是很幸運的,因為,以前散失的律書,日本多還保存著哩!今後,當有一番新的弘律的氣象出現了,但願真能出現這一弘律氣象。
第五節弘揚戒律的困難
弘揚戒律,我們雖希望它能夠出現新的氣象,然從歷史上看,卻是不太樂觀的;因為,一部中國佛教史,關於弘揚戒律的記載,在比例上的分量是那樣的輕。
我們檢討一下,戒律既為佛法的根本,為什麼在中國的佛教圈中,對它不感興趣?本來,戒律之在佛教,亦如法律之在國家,一個國家,如果廢棄法律的效用,這一國家的社會,將會發生不堪想像的恐怖與黑暗;佛教如無戒律的維繫,佛子的墮落與僧團的腐敗,也是意料中事。中國佛教雖不如律而行,仍能延續至今者,因為佛教的經論之中,處處都有戒律的強調,比如《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大涅槃經》、《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遺教經》等等。所以中國佛教雖不嚴於律制的遵守,但卻沒有違背戒律的重要原則,這是值得慶幸的事。但也正因中國佛教未能確切的如律而行,所以中國佛教的狀態,也在每下愈況之中。本來,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依法不依人的,只要依照律制而行,佛法自可歷久常新。然在中國的佛教,歷代以來,往往是依人不依法的,如能出現幾位大祖師,大家都向祖師看齊,以祖師作為佛教的中心,向祖師團結,佛教便興;如果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間,沒有一個祖師出現,佛教也就跟著衰微下去!佛教本以佛法為中心,中國的佛教,卻以祖師為重心,所以佛教史上的局面,總是起落盛衰不定,無法求得永久的平穩。
我們如要挽救這一缺失,唯有從建立戒律制度上著手,但是中國佛教的環境及其背景,對於弘揚戒律,卻有太多困難,過去如此,今後還是如此。現在分析如下:
律本太多,綜合不易:傳來中國的戒律,共有四律五論之多,其中各部廣律的制戒因緣以及戒相條文,相差不了多少,但其律論對於條文的解釋,各彰本部的宗義,互異的就多了;有的要求很嚴,有的要求頗輕,如果逐部看了之後,即使自以為是,也無法肯定已經是到什麼程度。因此,南山道宣律師,沒有見過新譯《有部律》的律文,他的好多觀點是相左於新譯《有部律》的。《有部律》雖後出,但以義淨三藏留學印度二十多年,遍考當時的印度律制,並作《南海寄歸內法傳》以用說明,他的觀點可能要比南山較為正確,唯其如今若以《有部律》而謗南山,又覺得尚有未可。再如明末清初的蕅益、見月諸師,因其未能遍獲南山以下的唐宋律著,雖然宗依南山,仍然未能盡合南山的觀點。今人如要治律弘律,首先必須衝破此一難關。
戒相繁複,不易明記:大家知道,佛法之中,以唯識宗的名相最多,最難一一明記,殊不知律宗也有如此的困難存在。大家知道戒律最少的是五條──五戒,最多的是三百四十八條──比丘尼戒。但此僅是條文而已,正像一個僅僅熟背憲法條文的人,並不即能成為憲法學專家。因為差不多在每一條的戒相之中,都有開、遮、持、犯的分別;同時,開、遮、持、犯,各各亦皆有輕重等級;同樣犯一條戒,由於動機、方法、結果等的不同,犯罪的輕重,及懺罪的方式,也隨著不同。戒律的條文固然是戒,凡不在條文中而仍違反了佛法原則的,也都算是犯戒。犯的是什麼戒?應當怎麼辦?這些都該瞭如指掌,始得稱為通曉戒律。尤其是一個比丘,不以知曉比丘戒的犯相輕重及懺悔方式就算了事,還應通曉大小乘的一切戒律,才算是明白戒律。所以研究戒律,首先必須付出耐心和苦心,從枯燥的戒相名目之中,培養出持戒的精神與弘戒的悲願來。
學戒弘戒,必須持戒:一個學戒弘戒的人,雖然不必事事如律而行,最少該是個戒律的忠實信徒,他雖未必持律謹嚴,至少是個嚮往著如律而行的人。否則他的弘律事業,也就難收到理想的效果了。
學禪的可以不拘小節,學律的事事都得謹慎。學教講經的法師,可以大座說法,可以廣收徒眾,可以名利雙收;持戒弘戒的律師,沒有大規模的僧團,講戒不必登大座,或有大叢林下,卻又未必歡迎你去講戒,學戒持戒的人,絕對不敢濫收徒眾,否則即是犯戒。因此,若要立志弘戒,必須先要準備甘於寂寞。當然,如能弘戒成功,影響所及,風吹草偃之時,這些問題,也就不成問題了。但是身為一個弘戒的人,他的生活必定要比一般比丘更為刻苦,他的資身用物,不敢過好,也不敢過多,否則便是犯戒。是以,如想發心弘戒,首先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中國環境,不崇律制:因為中國的佛教,尤其是南宋以來,根本喪失了崇尚律制的習慣,所以我們要在這不崇尚律制的環境下去弘揚戒律將會有很大的障礙,因為多數人不崇尚律制,也就討厭崇尚律制的人,唯恐會以律制的理由去約束他們或抨擊他們,使得他們無法安心。我曾聽人說過,因為弘一大師弘律,所以很多地方就不太歡迎他,甚至有人把他看成怪物。其實,大家都是怪物而不自知,反把非怪物者當成了怪物。試問出家的比丘,不過比丘的生活,不以為怪,反將一個過比丘生活的比丘,看成怪物,豈不怪得出奇!但是,無論如何說法,在此不崇尚律制的環境中,固有弘揚戒律的自由,也有反對弘揚戒律的自由!不便明謗,卻不能取消他人不予合作的自由!是故明末的蕅益弘戒,數講數停,最多的聽眾,也不出十餘人;近代的弘一弘戒,起初數度不如願,後來即以「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眾,不定地址」為其弘律的方案。
律文刻板,時代變更:戒律的條文是死的,社會的演變是活的。要以死板板的條文,硬生生地加在每一時代的每一個佛弟子頭上,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但在佛陀入滅之後,迦葉尊者曾經提出這樣的原則:「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大正藏》二二.一九一頁中)因此,歷代的許多大德,都不敢賦戒律予靈活適應的生命,而以印度人的觀念來規範中國人,以隋唐時代的觀念來規範現代人,寧可讓戒律廢棄一邊,也不願使其作時代潮流的適應。所以很多人以為持戒乃是迂腐落伍的行為。事實上,如果真的全部遵照條文而行,確也有一些問題。因為《五分律》卷二二中有如此的說明:「佛言……雖是我所制,而於餘方不以為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於餘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大正藏》二二.一五三頁上)可知佛的戒律,並不刻板,只要不違背律制的原則,即可隨方應用,自也可以隨著時代的潮流而應用,唯其如何隨方隨時應用者,必須熟習戒律之後,方可靈活圓融,方可不違律制的原則。時代有新舊,律制的精神則是歷久而常新的,不能泥古不化,更不能因噎廢食。但此卻是弘揚戒律的一大暗礁!
以上五點,都是戒律不弘的主要因素,可是我們不能因了困難、因了障礙,便將弘揚戒律的任務停頓下來。有了困難,便應找出困難的原因所在,既然找出了困難的原因所在,就該設法解決,當克服的克服,當疏導的疏導,以期群策群力,弘揚戒律。
第六節培養學律的風氣
要想今後的中國佛教,有穩定性,有組織體,有團結力,必須積極於律制的推行;要想中國的僧團,有統一性,有制裁權,有活動力,必須推行律制的教育;要想佛教徒們,層層相因,彼此節制,保持身心的清淨,達於離欲之境,必須教育大家,使得人人受戒學戒並且持戒。
弘揚戒律的工作,立基於大家的受戒學戒與持戒之上。不先受戒,則不能學戒;若不學戒持戒,也就無戒可弘。所以佛制規定,新出家的比丘,最初五夏,必先依止學律;若不能夠知解戒律的持犯輕重,便不得離師,便不許為人之師。
目前,要想學律,困難還是很多的,除了沒有理想的道場供人學習,也沒有充分的律書供人閱讀,有許多的律疏律鈔,多在《卍續藏經》之中,因為國內沒有翻印《卍續藏經》,也未能使那些律書單印流通,要想借閱也是不太容易辦到。案:《卍續藏經》,已於一九七一年臺港佛界合作翻印完畢)
根據弘一大師的意見,認為能將他所編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及道宣律師的《四分律含注戒本》與《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共三部書研究完畢,便可了知一個律學的大綱。但那僅僅是《四分律》而已,其他各部,仍然無從瞭解。
因此,我總覺得,我們還缺少一部戒律學的入門書籍,所謂入門書籍,那該是一般性的,通俗性的,同時也應該是時代性的與實用性的;這是我寫本書的動機。可惜,我的才淺力絀,尤其我也不是能將戒律精神從我的生活中全部表達出來的人,寫來總是力不從心;何況我所讀的律典,也是極其有限。所以,本書雖然名為《戒律學綱要》,實則,僅是我在兩年多中學習戒律的一點心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