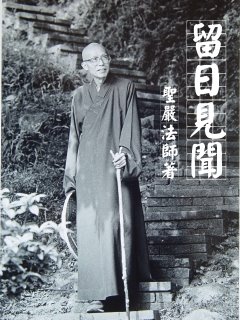
上篇
留學見聞
初到東京所見的日本佛教
初到異國,由於所見所聞不廣不深,對於異國佛教的置評,可能有失公允。但對一個突然置身於另一國土中的僧人而言,以自己的立場,將所見的片段向關心的祖國師友們,做一點介紹,那是無可厚非的。
實則,當我未來日本之前,對於日本佛教的趨勢及其現狀,已由友人的口頭和日文書刊的報導中,大致已有一個印象,此在三月十二日晚上,善導寺召開的惜別會上,我已做了分析,那就是:
上層建構的佛教學術研究化:由於一百年前明治天皇維新運動之時,實行「神佛分離」政策,此與中國史上的「尊王攘夷」運動相似,目的在於排斥佛教,消滅佛教的僧人,迫使僧人變為神道教的教士。因此而激起日本佛教的革新機運,各宗,尤其是淨土真宗,派遣優秀青年至歐洲留學,學習佛典的古文字─梵文和巴利文,學習西洋的治學方法和治學工具(語文),這些知識分子返日後,即為日本佛教帶來了新的命運。各宗紛紛創辦大學,培養後繼的人才,因此而出了不少知名於國際的佛教博士,佛教學術化,也就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日本佛教徒之不致流於盲從的迷信,此乃原因之一;日本佛教之不受基督教的侵蝕,此亦因素之一。凡是佛教徒,多少均能知道他們所信這一宗派佛教的若干教義。我來東京之後,最先接觸的是書店,使我驚奇的是每家普通書店,幾乎均特別為佛書闢出一個陳列的部門,在火車上也可經常看到日本人士捧著一冊佛書在看(日人的讀書風氣極盛,在車上,即使是短程乘客,看書看報不算稀奇)。當我去神田的神保町,書店書籍之多,若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來比,是無法相比的;再去東京大學的赤門前,參觀山喜房佛書林,它的門面雖不大,店中的新舊版佛書,多得使我欣喜不已。日本的佛書,大致可分兩大類別:一類是通俗化的勸信的佛書,每版可以銷售數十萬冊的也有,所以很便宜;一類是專門化的研究性的佛書,僅為學者提供參考和研究的,所以銷數很少,往往一版僅出五百部或一千部,因此非常昂貴。
不過,佛教走上純學術化的路子,雖能為時代的知識分子所喜,卻也未必就是佛教的佳音,因為一般佛教學者,既重於文字的考證比觀推理,不免對宗教信仰的虔敬和佛法的親自實踐實證,就要大打折扣。但此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有一位教授,他在學校的講臺上,是研究性的、純客觀的,一回到他所住持的寺院,他也誦經禮拜,對自宗的信徒講道,又放棄客觀而站到他這一宗的立場了。
這在我看來,他是過著矛盾的雙重人格的生活,然他已習以為常,此亦正是我所尚未理解的日本佛教問題之一。
一般建構的佛教信仰世俗化:如眾所周知的,今日的日本,已少有男青年走上純出家的比丘之路;在幾年以前曾因少女出家太多而加限制,今後的日本少女出家,可能也像臺灣一樣,越來越少。有些尼寺的老尼,正為找不到後繼尼弟子而焦心。因為這種趨勢,雖然由來已久,自淨土真宗的親鸞和日蓮宗的日蓮以後,日本僧人漸漸走上蓄妻生子之途,明治以來,此一傾向更盛,其他舊宗派的僧人生活也被世俗同化。僧人住持寺院,即以寺院為家,並以長子為住持寺院的繼承人,其餘子女則另向寺外的事業發展。僧人住寺,仍須另謀兼職,住持成為累贅,致有以生為僧人的長子而覺得不幸。因為,近數十年來,日本佛教變化太大,蓄妻生子的寺院僧人,在我中國人看來已是新得離了譜,然而其他新興佛教教派如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孝道教團等看他們,又覺得太過落伍陳舊了。例如創價學會攻擊舊宗各派的寺院僧人,為只知要錢不行正法的分子,信仰僧人毫無意義。新宗派大多是由日蓮宗分化而出現,看他們的作風,無疑是以佛教的教綱為中心,卻以基督教及天主教的方法為手段。主張他力得救的信仰,崇拜《法華經》,持誦「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經題,就是得救之道,他們鼓動狂熱的信力,並發動所有的信徒,在大眾之前,說出信仰之後所得的經驗,此與基督教的所謂「見證」,如出一轍,但此功效極大。
我到東京之後,參觀了幾所舊宗寺院,這些寺院,大多已成遊覽區,靠收取遊客的門票來維持,有些小寺院,看來衰象畢露,了無生氣,大殿的門戶緊閉,殿旁住著寺僧的妻兒,除了一年幾度的法會,平常很少有信徒上寺敬香。但此並不表示這些寺院沒有信徒,也不表示他們的信徒信仰不夠虔誠,乃是工商業社會的生活,使得所有的人們不容易抽出時間來上寺院禮拜。平日忙於工作,假日則做郊遊,或上百貨公司購物,或有私人應酬。因此,舊派各宗,已在式微之中,然其潛力的雄厚,仍非新興教派所能於短時期內代替的,至少舊派各宗,特別是淨土真宗,在今天的日本佛教界仍是站在主流的地位。
正由於日本的觀光事業發達,許多歷史性的寺院,均成了遊覽中心,我因初到東京,無心以觀光的身分去探訪名勝古蹟,同時人地生疏,無人導遊,所以在三個星期之內,僅到了淺草的金龍山觀音寺,以及鎌倉的八幡宮、建長寺、長谷寺、高德寺。此均由王心明居士導遊,我和淨海法師及慧定師,不負此行。我在臺灣時,即已聞名淺草及鎌倉兩處名勝,但對淺草的印象很不理想,據說那裡的情景,類似臺北巿的龍山寺,香火迷信的色彩較濃,商業攤販的陳設也很複雜。
可是,當我遊過淺草之後,感觸略有不同,至少,在淺草附近,有許多家大小不等的佛具店,規模最大的一家叫作翠雲堂,那是一家資本雄厚的大公司,是一座大廈,所陳列的金漆雕花的華蓋、長幡、金幢,琳瑯滿目,金碧輝煌,各式古銅色及金色、銀色的供燈、香爐、燭臺、供器、佛像,水晶、真珠、化學的大小念珠,大小不等的銅磬和木魚等等,由這家佛具公司,便可體會出佛教在日本的前途了。此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大陸,不易見到,在今日的臺灣,也要待之於大家的努力,始可與日本相比。
再說金龍山的觀音寺,初看確有點像龍山寺,但也頗有不同之處,至少龍山寺的氣派小得很多,而且神像太雜,三教九流的神像,幾乎均可在龍山寺內見到,致有使外人的印象生起一種「佛教就是這些神像崇拜」的錯覺。淺草觀音寺則不同,一到該地,遠遠地就見到巍峨的兩道大門之下,懸著兩對直徑數丈大的大燈籠,使你走到下面就覺得佛力的偉大,對照著自我的渺小。走上佛殿之前,有一個大香爐,專供香客敬香之用,敬完香再登上臺階,進入大殿禮佛,殿內空曠寬大,香客無不虔敬肅穆,默默祈禱,未見喧嘩嘻笑、人聲嘈雜的現象,他們進了佛殿,就像是面見了佛菩薩。這種情形也使我深受感動,當然,日本的佛教,本與日本的神道教,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所以佛寺中兼售護身符咒及護身的小像,也很普遍,信徒到佛寺中請僧人做消災降福的儀式,也很尋常,我在淺草及鎌倉都見到了這種純信仰的宗教儀式,尚有在鎌倉的鎌倉宮,見到了由僧人主持的日本舊式的結婚典禮,可見日本佛教世俗化的程度,也說明了他們的信仰是與人民的生活打成一片的。不過由於時代的進步,社會生活的變遷,舊宗的若干形式已和時代生活出現了脫節的現象,致使信徒與寺院之間日漸疏遠,唯有利用郊遊覽勝的機會,到各處佛寺致敬了。
說到日本的佛教古蹟,頗使我感慨,記得我在上海靜安寺求學時,明知該寺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卻無歷史的遺痕可見,日本人對於古蹟古物的保存保護,則是如此的用心。
例如建長寺建於建長五年(西元一二五三年)的北條時賴之世,一口梵鐘,雖經過足利時代(西元一四一五年)的戰火而燒毀了寺舍,梵鐘卻歷七百一十六年而迄今無恙,掛在那裡成了導遊小姐向遊客津津樂道的國寶。寺舍於元和元年(西元一六一五年)的德川時代重建,如今的那座古殿,以及殿內的佛像不加修飾,仍以古老的姿態聳立在那裡,殿內不准遊客進入,僅能站在殿門外瞻仰。
另有長谷寺的十一面觀音像,高達九公尺,是與奈良的長谷觀音用同一株楠木雕成於西元第七世紀的行基大師時代,此像含有高度的密教藝術的色彩,莊嚴雄偉,殊為珍貴。
鎌倉的大佛,已是聞名世界的日本國寶,是以重達九十四公噸的青銅鑄造,高達十一點四公尺,這尊阿彌陀佛的坐像,雖不及臺灣彰化的八卦山大佛高大,其藝術價值則遠超過彰化大佛。此尊銅佛造於建長四年,相當中國南宋時代,當時供於殿中,後來殿舍毀於天災,佛像便露座迄今。
自鎌倉返回東京市區的途中,經過橫濱,菲律賓的劉梅生居士,主張順便參觀一下天臺宗的新教派「孝道教團」的本山──孝道山,這個教派與臺灣佛教界頗有聯繫,一九六五年曾經由其正副統理率領訪問團到過臺灣,所以我們一去,說是來自臺灣,他們表示非常歡迎。由正副事務長至正副統理(教宗)均來接待我們,最難得的那天是四月五日,他們為了迎接四月八日的「花祭」──即是浴佛節,正忙於一連三天的慶祝節目的準備及安排,他們在忙得團團轉的情形下,竟能把禮服穿得整整齊齊地陪我們談上一個多小時,並且堅持要留我們吃了晚餐再走,結果由於橫濱的幾家料理店(菜館),來不及臨時做素菜而作罷,我們辭別之時,每一個人都得到一份禮物和一些書刊。看樣子,孝道山也學會了我國的人情味了。
孝道山是受天臺宗本山比叡山傳承的新宗,它的統理大僧正也是出身於天臺宗,但它自昭和二十七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創立以在家佛教為主旨的孝道教團以來,已有四十萬信徒,分支教會一百四十所。其組織龐大,人才很多,自己辦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好幾所,信徒的活動,設有壯年會、婦人會、青年會、健兒隊。這個教派的實力,在四月六日的花車遊行之中,充分地表現出來,那天上午特地趕到橫濱市櫻木町,看孝道山為慶祝佛誕而預先舉辦的花車表演,由橫濱公園行至蒔田公園,全部隊伍表演通過長達兩小時,共分鼓笛隊、青年男女菩薩隊、大鼓及小鼓隊、幼兒隊、外國的錫蘭人隊、中國的龍隊,其次才是二十八輛花車,每一輛花車便是一個佛教故事的表演,由花車的故事可以明白:他們的中心信仰是釋迦世尊,崇拜的日本高僧是傳教大師。他們在這遊行隊伍中,顯示出了物力和人力,服裝、道具均是特製的,尤其是青年男女菩薩隊的女青年和男青年,那樣的多而整齊虔敬,最使我欣喜。
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在家佛教教派,岡野正道及岡野貴美子是一對夫婦,但也就是孝道教團的正副兩統理,他們的兒子岡野正貫、兒媳岡野貴子,便是孝道教團的法嗣,少夫婦兩人均是得有美國學位的中年人。這是日本在家佛教世俗化且世襲化的特色,也許他們另有一套完美的制度,否則我想,假如法嗣(子孫)之中出了一個敗家子,這個家族化的教團,豈不也會因此結束了嗎?但是,淨土真宗的家族化,已有數百年,仍能維繫發展,可見他們的家族世襲,並不就是私情的授受了。
四月六日,正是星期天,王心明居士約我和淨海、慧定二師,還有劉梅生居士,去參觀位於中野區的「立正佼成會」聖堂,這是一個日蓮宗的新教派,成立迄今(西元一九六九年)不過三十一年,但是它的本會會所的「聖堂」,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教教堂,建坪九千多坪,分為上下七樓,可容三萬五千人同時參加誦經或聽經,平日每天上午均有五、六百人前往參加誦經,星期天則有一、兩萬人。在日本的分支會所有一百六十座,會員已超過三百萬,在美國的洛杉磯和夏威夷,均已設立分會。可惜那天的聖堂負責人不在,僅由一位會員招待我們,做了簡單的介紹和說明。我問他,佼成會有沒有向臺灣發展?臺灣是否有了他們的會員或分支會所?他則笑稱尚不明白。
佼成會的聖堂,耗資四十億的日圓建成,相當新臺幣四億四千萬元,所以建築得極為富麗宏偉,初看類似回教寺院,又像天主教的聖彼得大教堂,仔細研究,卻又處處含蓄著佛教的意識,正門上楣的三座聖像浮雕,是文殊、普賢、彌勒,殿中所供是釋尊立像,那位會員特別向我解釋那尊立像是丈六金身,身長一丈,頭長六寸。佛前的供具,無一不是經過特別設計的。聖堂的牆壁,我以為是大理石,但他告訴我那不是大理石,是在九州新開採成功的一種寶石。
佼成會雖與創價學會同為日蓮宗的新教,但它不做政治活動,不介政治紛爭,至少在目前尚未見到它的政治色彩。他們的每日集會儀式,類似天主教,殿內不設拜具,信徒到時,僅合掌向上問訊,不燒香。臺上由一人主壇,四人陪同,主壇者舉腔,其餘隨同誦念,只用磬做起結訊號,不敲木魚。大家坐在椅子上,像是大戲院的排椅。佛事的開始和結束時,由一隊唱詩班的青年男女合唱讚歌,大家隨聲同唱。念經時,人手一部《法華經》的節本,跟著主壇者同誦,不快不慢,和和平平,千人一聲,萬人一聲。有些信徒已能背誦,合掌端坐,朗朗虔誦。他們平日至聖堂的目的,便是參加集體誦經。
誦經完畢,男女會員分開,大家分組上樓,席地而坐,十數人一組,每組有一位指導人或召集人,由大家提出在生活上與信仰有關的問題,懇切地互相討論。此外尚有特定的各種活動組織。但我所見他們的會員,也是婦女多於男士,據稱星期天到的男士已比平日為多了,可見不論中外,男人的宗教生活的機會,遠不如女人為多。
最後我願敬告國內的同道:日本佛教走向通俗化及世俗化,確有其可取之處,但在我們中國,這個現象還不適宜來得如此之早,中國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淵源,均不同於日本,所以若要振興中國佛教,仍宜於比丘中心的出世化。我們今天所要向日本學習的,主要倒不是學術化,而是如何地激起民眾信仰的熱忱,如何地使得佛教的信仰與現實的民眾生活配合起來。其次才可談到學理的研究,當然,若無學理的高層教育,一般的信仰也是無法可大可久的。(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佛教文化》季刊一二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