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華山歷史上的佛教人才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地藏比丘金喬覺(西元六九六~七九四年),已在前面介紹過了。金地藏能作詩,唐代九華也出了應物、神穎、冷然、齊己等幾位名詩僧,均有詩作遺世。
其次為五代的詩僧圓證,曾經住於臥雲庵,主持九華詩社。
南宋時代的大慧宗杲(西元一○八九~一一六三年)曾經朝禮九華山,並傳臨濟宗旨,根據清德宗光緒年間(西元一八七五~一九○八年)《九華山志》記述,宗杲圓寂後,九華山尊其為定光佛,所以歷來的《九華山志》都收有宗杲的〈遊九華山題天臺高處〉詩,現抄錄如下:「踏遍天臺不作聲,清鐘一杵萬山鳴,五釵松擁仙壇蓋,九朵蓮開佛國城。南嶺俯窺江影白,東岩坐待夕陽明,名山笑我生天晚,一首唐詩早擅名。」
明末的性蓮禪師(西元一五四三~一五九七年)在明神宗萬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被九華山請為叢林之主,居於金鋼峯,他圓寂之後,憨山德清為其撰墓誌銘。
海玉禪師(西元一五一三~一六二三年)在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來九華山,住於東崖摩空嶺,以野果為食,用舌血和金粉,費時二十餘年,抄寫《華嚴經》八十一卷,圓寂後肉身不壞,裝金供於庵內。明莊烈帝崇禎三年(西元一六三○年)冊封海玉為「應身菩薩」,迄今仍供奉在百歲宮裡。
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他可以說是明末佛教界著作最多的一位高僧,他於崇禎九年春到十年秋為止(西元一六三六~一六三七年),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住在九華山。在那裡讀了一千多卷的藏經,並且撰寫了《梵網經合註》七卷,以及《梵網經玄義》一卷、《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性學開蒙》一卷,同時又撰寫了一篇〈壇中十問答〉。不過在這段時間,過的日子並不舒服,住的、吃的、穿的,都很簡陋艱苦,而且經常害著九死一生的大病。他在九華山的生活情況,除了第四篇中已介紹的,還有如下的記載:
《四書蕅益解‧自序》有云:「逮大病幾絕,歸臥九華,腐滓以為饌,糠粃以為糧。」
《自像贊二十三》有云:「年至三十八,大病為良藥,高臥九子峯,糠滓堪咀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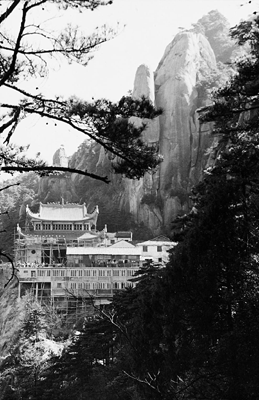
▲增建中的拜經臺及大鵬聽經石。
《山居六十二偈》中有云:「一病五百日,形神竝已枯。緇素偶相值,稱我為禪癯」
在《自觀印闍黎傳》中有云:「法友信我於舉世非毀之際,從我於九死一生之時。」(此時蕅益大師正住於九華山)
從以上所引的資料可見,蕅益大師在九華山中的生活情況,極端艱苦,但是他還能夠不斷的看藏經、著作、拜懺、持咒、講經,以及與僧俗詩友做文字的開示。像他這樣為法忘軀,堅貞卓越,不被病苦所屈,不受生活條件影響的出家人精神,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當時蕅益大師是住在什麼地方呢?根據他的《絕餘篇》第四卷,知道他是住在華嚴庵,以及九子別峯。
華嚴庵就是坐落在現今東崖華嚴嶺頭的華嚴禪寺,又稱回香閣;清文宗咸豐年間(西元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毀於兵燹,經過幾次的興毀,現在只是一間二百一十八平方米的小庵。至於九子別峯,目前是一座已廢的寺院,原來是化城寺的庵房,建於明末,名為九子閣。因為我在日本寫博士論文,就是研究蕅益大師,所以對他在九華山的情況比較熟悉,我對蕅益大師的心境也比較能夠體驗,他對中國近世佛教的貢獻和影響,直到現在猶存。所以我到九華山,雖然沒有親自拜訪他曾經住過的地方,但是我相信許多的場合,我們都是踩著他的足跡在走。
此後,到過九華山的近代高僧,我就不多介紹了,例如月霞、弘一、圓瑛、太虛、虛雲、白聖等大德,都曾朝禮過九華山。尤其是白聖長老,他領導臺灣佛教數十年,他是我靜安寺佛學院的副院長,也是我受具足戒的開堂;他便是在九華山的甘露寺落髮出家,又於祇園寺秉受具足戒。
當天下午,我們就離開九華山返回南京,晚餐是在國際會議大飯店,夜宿金陵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