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雲居寺.石經山
房山石材艾葉青
四月十三日,星期六。
早上八點半出發,車行兩個小時,才到達雲居寺。該寺位於北京巿西南郊七十公里處的房山縣境內。發現北京人頭骨的周口店,就在它的左近;出產可口而香甜板栗的良鄉,則在它的右近。
至於房山的出名,是因盛產品質優良的石材。例如北京的天壇及故宮所用的大批漢白玉建材,就是出於房山。另外一種作為碑刻之上品的石材,名為「艾葉青」的,也出在房山。而且房山的遍地,都是大理石。所以,在雲居寺石經山前方的一個盆地,被命名為「石窩」。這三種石材之中,大理石遍布地面;其他兩種深藏地下,表層覆以土壤,若要開採,就得像穿井開礦那樣的向地下發掘。據說,近世以來,已停止開採。
從以上介紹房山出產優良的石材,始知從隋朝開始,歷代的大師們為何要選擇房山這個地方建寺而雕刻石經的原因了。
我們長途跋涉前往該地的目的,就是要親眼一睹雲居寺石經山的石經窟。我們到達該地時,首先在雲居寺的接待室,跟當地的幾位首長及管理人員見面,他們是房山區文化文物局長、房山區區委宣傳部長、房山區旅遊事業局長、雲居寺文物管理處主任,及後到的房山公安局長。
那天的天氣晴朗,但在雲居寺感到蠻冷的。我們草草吃光隨身攜帶的餅乾、饅頭,算是用了午餐,便趕往距寺院有一公里半之外的石經山。
本團的冉教授,曾經去過石經山,知道山上沒有什麼可看,所以留在寺內休息。雖然當地導遊告訴我們,從山麓到山頂只有五百多公尺,冉教授卻事先預告我︰「要有心理準備,那五百多公尺不是很短的路。」在我心想,那不過是十根電線桿的距離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吧!
石經山石刻佛經
在去雲居寺之前,我已有了一些石經山的資料。因為中國佛教協會負責出版全套的《房山石經拓印本》,當我一九八八年訪問大陸之時,就已買了幾冊;同時,在佛協的「法音文庫」之中有一冊《房山石經之研究》,該書收集了十一個人的文章,共十四篇。而這次從北京陪同我們去訪問的房山石經專家吳夢麟女士,就是其中的作者之一。
現在根據資料及我的見聞,將房山石經及雲居寺,介紹敍述如下︰北京西南一百餘里處,有一白帶山,屬太行山脈,高五百多公尺,以山嶺常有白雲縈繞而得名。又名莎題山,因為山中盛產莎題草。又因山中藏有石刻佛經,故稱石經山。

▲石經山正前方是石窩。
石經的雕刻工程,是起於佛教的末法思想,所謂末法之說,見於大乘經典如《法華經》、《大乘同性經》、《寶積經》、《大集經》、《月燈三昧經》等諸經。謂佛法住世,歷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期,最後法滅。南嶽慧思禪師相信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而隋世正好是佛涅槃一千五百年,因為剛經過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的滅法運動,佛教遭受到無情的打擊,所以在南嶽慧思禪師,就有末法時代已經開始的信仰。當時他的弟子靜琬,便擔心佛教很快就會被毀,所以發起了石雕佛經藏於山洞的運動。
雖說石刻佛經,在隋代之前的北齊時代已經開始,例如北響堂山、南響堂山的石窟內已經有了《文殊般若經》、《彌勒成佛經》、《華嚴經》、《般若經》等的石刻,但是,規模最大,延續最久的,要推河北省房山縣的石經山了。那是雲居寺的創建者靜琬大師從隋煬帝大業年間(西元六○五─六一六年)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遷化為止,一共經營了七個石室於其四壁及其室內嵌滿藏貯了石經之後便予封藏起來。這是有名的所謂「琬公七窟」。當時的主要施主是隋煬帝,參與工作的尚有玄導和僧儀。此後,於唐玄宗開元及天寶年間(西元七一三─七五五年),又得到玄宗第八妺金仙公主的資助,而由惠邏、玄法主持雕刻。到現在為止,在石經山的頂上還有一座金仙公主的紀念塔。由於帝王的信仰,所以大臣、地方官、百姓、也多多少少參與了石經工程的贊助。這樣的事業,又經過遼、金、元各朝,有七百五十年間的斷斷續續的經營,一共在山上開了九窟。其中以琬公七窟中的第五窟,又名華嚴堂或雷音洞,是其主要經典的收藏之處,其中藏有《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維摩經》、《勝鬘經》、《金剛經》、《遺教經》、《無量義經》、《彌勒上生經》等經。
石經山的九個洞分上下兩層,上層七個洞,下層兩個洞,上層的雷音洞,寬廣如殿,四壁鑲嵌經版一百四十六塊,嵌滿了四周牆壁。九個洞中,唯有此處是開放的,其他八個均以石門封固,近代經過開啟拓印之後,放回原處,重新加封。我們看到下層的兩個洞,在石門的上段,是用石板鏤空如窗,可以通過窗縫看到裡邊的石刻經版,層疊堆置。九個石洞,一共藏經四千一百九十六片。洞內外,尚有石經殘蝕碎片七百八十二塊。另一部分,是遼、金兩代所刻的石經,沒有藏在山上的石洞,而是藏在雲居寺南塔前的地穴之內,共計一萬零八十二片。合計是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八塊石刻,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佛經,共計三千五百七十二卷。綜合山洞及地穴石經的時代,從隋朝的大業年間開始,到明末結束,歷經一千餘載。從此可以看出,佛教的信仰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對中國人的精神所寄,是多麼的偉大和重要。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國佛教協會對房山石經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發掘、拓印的工作,歷時三載才竟全功。石洞原來沒有編列號碼,工作人員將下層的兩個洞從右起編為一及二號,上層的七個洞自右向左順次編號。名為華嚴堂的雷音洞就是第五號。當時發現其他七洞雖然封固,而第三號的洞門破壞非常嚴重,現在已經修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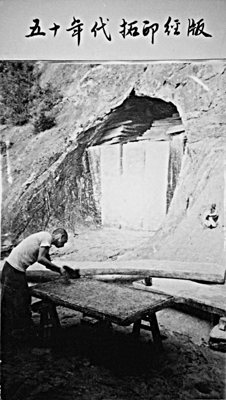
▲石經山五十年代拓印經版。
九個石洞大小不一,所藏經版也多少不等,除了嵌於四壁的,其他經塊,一般是,下層豎立排放,上層橫放和平放,並無一定的規律。那些經版的尺寸,大致可分三種類型︰1.大型者長二米五十公分,寬六十公分;2.中型者長一米六十公分,寬六十二公分;3.小型者長四十六公分,寬七十六公分。

▲石經山藏經洞第一窟。
我們一行從山下往上攀登之時,再問嚮導人員︰「五百多公尺,那有這麼遠?」因為那天的天氣非常晴朗,又是週末假日,登山的中、小學生和旅遊的民眾,在山路上密密麻麻。有許多青少年學生,不走正路,只是攀著山石,像蜘蛛似的上山,手腳並用,爬到山腰之時已經像是一隻一隻的螞蟻。五百多公尺的距離怎麼可能有那麼高?結果所得到的答案是︰「石經山的高度是海拔的高度,並不等於山路的長度,所以登山實際需要的時間通常是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如果是老年的人,應該是要花一個小時。」
我應該也算是年老階段的人,可是,我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一邊聽著吳夢麟女士介紹房山的風物、歷史,以及她已經到石經山二十多次的經驗,一路上邊說邊走,就這麼爬了上去。到了山腰,有一座可以作為旅客歇腳之處的小院落,我在那邊見到了看守石經山的一位老人孫先生。他正在照顧著山上的各種設施,看來滿臉風霜,可是兩眼炯炯有神。當地的年輕導遊稱吳夢麟為吳老師,也稱那老人為孫老師,而當地人習慣,被稱老師未必教書,乃是對年長者的尊稱。我們在那座小院的屋子裡面坐了幾分鐘,繼續向上,石經洞已經遙遙在望。到此為止,已經爬了二十分鐘的所謂山路,其實僅是由人們走出來的天然小徑,並沒有石階,也沒有鋪上石條或磚塊,如果是遇到雨天,可能無法攀登。
再往上走,發現了數十公尺人工修築的石階步道。在走上石階之前的左側路邊,有一口井,好像直到現在還是活的。井口加了鐵蓋,上了鐵鎖,以防遊客污染破壞。據說山上的那位孫先生,平常就是飲用這口井裡的水。在如此高的山上,竟然有井,而且真的有水,不可思議。
繼續往上攀登,經過五分鐘,就到了石經洞的範圍。在上下兩層之前,都有人行的步道,以供遊客憑弔。我們在下層的兩個石洞之前合掌禮敬的同時,發現洞前的一塊巨石面上刻著﹁念佛﹂兩字。不知是那一代的作品了,它的字體並沒有石經版上那樣的強勁有力,也不那麼優美,想是後人刻的吧!不過用意倒是很好。
接著向上走,約二十公尺,便是上層。發現在洞口有幾座都是刻著《金剛經》的石碑,碑面雖然已有一些斑駁及人為的損壞,但其字跡還是非常的清晰可辨。每一個碑頭上方,刻有雙龍以及一個佛龕,龕中或者刻著一佛二菩薩像,或者只有一尊佛像,佛龕的兩側邊框都有題字,其中一個是「清信女宋小完敬造上」,「金輪[髟-(彰-章)+至]神皇帝及四生父母」;另外一個是「朝議郎行幽州范陽縣令」,「平輿縣開國子袁敬一經之碑供養」。碑的正背兩面都刻滿了經文。未暇考察那是屬於那個年代的文物。
雷音洞的佛舍利
前面已經說過,石經山九個洞中,開放的只有第五窟的雷音洞。我進洞之後,發現洞中有一張供桌,桌上有一紙說明,僅僅寫著「佛舍利發現處」,我立即五體投地拜了下去,同時也在此感受到靜琬大師以及歷代先賢的護法之心,那樣的懇切至誠,真是堅逾鐵石,固若金湯。如果沒有堅固的信心和高超的道行,豈會來做這樣的傻事。當年刻經和藏經的事業之艱難,可以由我當天登山的過程約略的體會一、二,石板是從十幾公里之外的石窩開採,雕琢、水磨之後,用人力運上山去,再逐字雕刻成文,而且字字工整,秀麗有力,所花的心力、體力、財力,是無法估計的。這不僅使我感受到佛教感化力的強大,更能使我感受到如果沒有歷代的先賢從事如此堅貞的護法運動,佛教也真的會滅亡。所以一時間,不顧旁邊還有許多的人,幾乎失聲痛哭起來,匍匐在地,久久站不起來。

▲作者在雷音洞內感恩先賢的護法精神,匍匐在地失聲痛哭。
至於說到佛的舍利,根據雲居寺現存〈大遼燕京涿州范陽縣白帶山石經雲居寺釋迦佛舍利塔記〉有如此的記載︰「原其舍利於東峯石巖名花嚴堂,苑法師秘此堂石柱內,後因修飾,得獲琉璃瓶內有舍利三百餘粒,晝夜放光,一月有餘。」這是說靜琬大師因為刻石經三百餘軼,而在山上開鑿華嚴堂,將佛舍利,密藏於柱,後來為了修飾而開啟石柱,即在琉璃瓶內有三百多顆,曾經放光一個多月。又據說,當明末紫柏大師到雲居寺石經山,開啟舍利盒,發現只剩下三粒。此事聞於明神宗的母親慈聖太后,而被請入宮中供養。發還之時,紫柏大師沒有開啟檢驗,僅僅附上一張紙條謂︰「某年某月某日由慈聖太后恭送還山,未予啟蓋檢視。」簽上紫柏的名字,便重行封藏起來。到了現代,有人把它打開,發現裡邊只有兩顆舍利,另外一顆是珍珠。對於紫柏大師的智慧,大家無限的讚歎,他這樣的作法,既對慈聖太后表示尊重和信用,也對後代做了交代。紫柏大師是我非常敬仰的人,他對中國近世佛教的貢獻與其他的蓮池、憨山、蕅益等三位,並稱為明末四大師。如果沒有他們四位大師在明末出現,今天中國的佛教已是另一種局面,甚至當說不堪設想。我能親身來到紫柏大師曾經踩過的土地和石頭上頂禮膜拜,禁不住使我感到無限的悲愴。這是我在大陸訪問途中感受最深的一天,佛法的偉大、法滅的危機,以及先賢的事蹟,縈繞腦際,感慨萬千。

▲〈石經寺釋迦佛舍利塔記〉碑文。
當我噙淚禮拜之後,細覽雷音洞四壁的石經,已有好多遭到了破壞,雖然也經過累次的重修、整理、拼湊、鑲貼,可是痕跡非常明顯。據說在一九五六年清理之時,發現壁上鑲嵌的經版已經脫落了十八塊,有的已經踩成碎片,甚至有許多殘破經片已被當作磚塊來修補牆角的土坑,而且也遭到自然風化的損壞。有些經版移動之時即成粉末,有些經版表層鼓起,稍一接觸即行剝落。好在「艾葉青」這樣的石材,最能耐得風化,大部分還是非常清晰。
在雷音洞中,豎有四根同為用艾葉青石材雕琢成功的石柱,頂天立地,好像是樑柱,其實是裝飾。每柱有八稜,形成八面,每面分成十七欄,每欄刻有兩個佛龕,每龕有一尊佛像,每尊佛像之旁都有名號,共有一千零八十八尊,刻工精緻,加上彩繪。這四根石柱,應該另有名稱,叫作「千佛幢」。這種表現,在大同的雲岡石窟中,也可見到。
上山一趟,身歷其境,畢竟不虛此行,當我下山之時,心境相當歡暢,放眼流覽四周的環境,發覺石經山是在三面環山的群山之中,據說原來是一片森林地帶,經過一九五○年代的濫肆砍伐,而成了一座荒山。近幾年來,正在加緊植樹,也僅在道路兩旁,可以看到頭兩尺高的柏樹,尚在石縫和乾土之中掙扎求生。向遠處望去,都還是濯濯的童山,向前延伸。因為當地氣候還是很冷,在群山的凹處,尚可看到若隱若現的幾處雪景。
雲居寺重建
從石經山下來,又回到了雲居寺,該寺坐落於白帶山的西南麓,創建者也是隋之靜琬,到遼聖宗的時代(西元九八三─一○三○年),已經有了五大院落、六進殿宇,兩側有配殿、帝王行宮及僧房。該寺坐西朝東,依地形之高下,建築殿堂,錯落有致,寺之南北有雙塔對峙。可惜在一九四二年,遭日軍砲火擊毀,幾乎全部夷為平地,僅剩南北兩座磚塔及碑刻等遺跡而已。
一九八五年,大陸以保護文物而撥專款並得到國內外佛教界人士的支持,在廢墟上重建雲居寺。如今已有五處殿堂恢復,開放旅遊。現在的管理處主任田福月,見到我時,合掌為禮,並且強調,他雖非僧人,卻是為了護持佛法而在努力,也盼望得到海外佛教徒的資助。現在的雲居寺,是依據「大清營造則例」建成,幸好該寺布局的原貌,還留有一張全景圖片。所以新建的殿堂,排列及配置不會與原寺有太多的出入。在它的中軸線上,從山門起是︰天王殿、牌樓、毘盧殿、韋馱殿、釋迦殿、栴檀殿、藥師殿、彌陀殿、最後是大悲殿。中軸線的北邊,有僧房兩幢、行宮四幢、千佛殿一幢;在中軸線的南邊,有文殊殿、地藏殿、祖師殿。原來在中軸線的兩側,應該還有其他的配殿,現在還未建成。連中軸線的兩側廂房也還沒有開始建築。不過在牌樓的兩側,鐘、鼓二樓,已經建好。
它的古蹟,就是南北兩座古塔。南塔建於遼代,密檐式十三層,可惜在抗日期間被日軍摧毀,現僅存塔基。北塔的下部為樓閣式,中空,有蹬道可登,上部是覆鉢形,有輪相及寶鼎,也是遼代所建。而其基座,可能是隋唐的遺物。
在北塔的東、西、南、北四角,各有一小塔,為唐代的建築。西北角的四方形小塔,塔頂為密檐式七級浮屠,通高四米有餘,塔門朝北,內有龕,正面浮雕一佛二菩薩,體型豐腴,線條柔美,為典型的唐代造像;東南角的四方形小石塔,唐睿宗太極元年(西元七一二年)所建;東北角小石塔,建於唐玄宗開元十年(西元七二二年),為方形,重檐六層,有奔象馳鹿,金剛力士及佛龕內的一佛二菩薩的石雕,都是盛唐的風格;在西南角的是開元十五年所建。
雲居寺現存遼塔有五座,其中三座為磚塔,兩座為石塔。開山琬公大師的塔,高兩丈餘,其中安有靜琬的靈骨,是遼道宗大安九年(西元一○九三年)所建,根據靜琬大師塔銘記載,琬大師於唐太宗貞觀十三(西元六三九九年)年圓寂之後,靈骨始終沒葬,至遼大安初年,有位通理大師,繼其志,而為之建塔安靈骨。也可以說,雲居寺的古蹟,除了洞窟及地穴發掘出來的石經之外,只有這些古塔而已。
現在雲居寺的石經館,是古代所沒有的。因為他們把遼塔前側地穴裡發現的遼、金時代的石經,全部都藏於石經館了。我們走馬看花,只見到那些跟石碑相同的石經,堆滿了一房子的木架上。同時讓我們見到《龍藏》的木刻經版,也都藏於該寺的石經館內,看來相當的古舊。但是,木質堅硬,所以字跡完好如初。
警車開導
我們參觀雲居寺的各項建築物及石經館時,處處都被我們的嚮導往前帶著奔馳,只聽到催促之聲︰「抓緊時間!抓緊時間!否則的話,返回北京的路上會有麻煩。」
所謂「麻煩」,就是交通阻塞。唯在十二日那天,就已經聽說,房山縣的公安局局長會親自帶著開導車來保護我們。此一消息使我有點訝異,我又不是什麼要人,何須驚動地方官府策動警車保護?我們的領隊說是為了禮貌;我們的陪團則說沒有什麼。但在我們到達雲居寺時,就發現幾輛開導警車停在寺門口,卻並未陪同我們上山。當我們在室內參觀之際,也沒有出動保護,想不到,在回程的路上就發現開導警車對我們太有用了。因為那正好是下午五點到六點之間,在房山通向北京的公路上,交通非常擁塞,有些路段,幾乎是寸步難行,如果不是警車開道,恐怕要在晚上八點之後才進得了城。當晚六點,我們卻要在頤和園宴客。東道主遲到,是無法原諒的事。結果由於開導車在我們前頭不斷的拉警笛,見車超車,不受交通號誌限制,一路上所有的車輛,不管東往或西來,都因我們而讓開。一直把我們送出了房山縣境,進入了北京巿的西南部,開導的警車人員才向我們揮手送別。
到此為止,我才恍然大悟,接待單位建設部,為什麼要房山縣作如此安排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