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紐約第五十次禪七
從密西根回到紐約後的第三天,那是十一月十七日,即在皇后區的法拉盛借到臺灣會館大會堂,做了一次公開演講,當晚雖然勁風挾寒雨,氣候冷肅,參加的僑界聽眾,仍是把會場擠滿。講題是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曾經講過的「情與理」。由於時地不同,內容也有些更動。
接著便是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一日之間,我在紐約主持的第五十次禪七。
回憶我在紐約打禪七的歷史,頗多辛酸,也極感欣慰。一九七七年五月的第一次禪七之後,我及我的幾位弟子,都渴望著能有另一次禪七的因緣,因為我們沒有固定的道場,是否還能借到場所,毫無把握。所幸沈家楨先生的菩提精舍,終年空著,而且地寬屋大,遠離塵囂,鄰近海灣;陸續地借到四次,都很順利,到第五次時,已是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已離開美國佛教會,正是我在美國最最困頓的階段,沈先生依舊答應借用,但在那七天之中,我們過得很不平安。第一個晚上,精舍的管理工人便來興師問罪,說我們不該那麼晚了,還有人從外面進來,形同小偷。第二天來檢查廚房,說我們不該任意使用精舍的珍貴碗盤。第三天則拿著他自衛的手槍,對著我們威脅說:「如果誰再敢破壞精舍的骨董,他守護有責,就要不客氣了。」他所謂的骨董,是指這座古老住宅中的舊桌椅、老地毯、一尊泥塑像,只要輕微移動,都有可能受損。
我們知道這絕不是沈先生的意思,但是工人的耳朵尖,心眼小,總是從何人口中聽到有關我的什麼批評了。所以我一再向他保證並且道歉,同時約束弟子們,盡可能地小心翼翼。總算讓我們打完了禪七。然在最後一晚的心得報告時,幾乎每一個人都哭了,認為佛法難遇,修行難得,尤其對於我的感激,情溢言表。第二天我們離開菩提精舍時,都有無限的感謝與感慨,有一個弟子噙著淚珠問我:「師父,我們不可能再來菩提精舍了,是嗎?」我安慰他:「我們學佛的人,相信因緣,不必強求,也毋須失望,未來的事,到時候再說吧!」我乘坐一個黑人弟子奧斯華‧佩爾(Oswald Pierre)的車子回紐約市,另一位中國弟子王明怡君也同車坐在後座,一路上大家靜默無言,好像尚在禪七的禁語期中,我偷眼看看他們,他們的雙眼,都滿含著淚水。迄今為止,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們兩人流淚。那位黑人並非有錢,但是一回紐約,就捐了我二千美金,而這兩人直到今天仍是我們禪中心的忠實會員。也可以說,我之留在美國而不辭辛勞,不畏艱難,受了這批弟子們的感動,也是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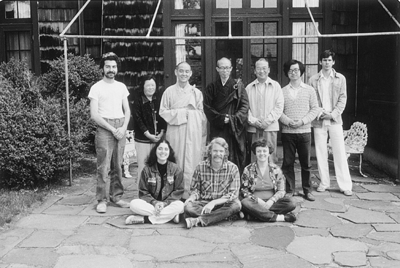
▲在菩提精舍第一次禪七滿日當天,沈家楨夫婦來慰問。後排左起:丹瓦塔、沈夫人、日常法師、作者、沈家楨、王明怡、保羅.甘迺迪。前排左起:麗契艾爾、丹史蒂文生、阿蘭卡,另一位拉菲雅白菲亞正在拍照。
當然,我們與菩提精舍的因緣,就此落幕。事後沈先生知道了一點什麼,特別向我致歉,並歡迎我們放心地再去打禪七,我倒不在乎,我們的會員卻不敢去了。如今的菩提精舍為了建設莊嚴寺而已經易主易名,那位工人則隨著宅院被沈先生讓給了新主人。
一九八○年春天,我們雖已購得一棟二層樓房,但還有兩戶房客,所以商借應行久夫人金玉堂居士的大乘寺,舉行第六次禪七。那是距離紐約市一百五十英里處的北方,被稱為紐約上州,靠近州政府所在地阿爾巴尼(Albany)之東。佔地面積相當大,新建佛殿可容兩三百人,設備完善。應夫人也親自參加禪七,並且帶同她的侍女為我們提供餐飲,這是我們禪七生活中最豐富、最順利的一次,真是感謝。然在結束之後也聽到了不再歡迎的風聲。直到去(一九八九)年初,應夫人始知此傳聞,便特別向我解釋,根本不可能有此一說。

▲作者在紐約舉行的第五十次禪七。
也許這就是我自己的業報,沈先生及應夫人,對我個人及我們的團體,都是恩人,偏偏會先後發生這樣的事,真太遺憾了!這也就是後來我要說:「若要傳宗接代,鳥須有巢、人當有家、僧該有寺」的原因了。
從一九八○年下半年起,東初禪寺的二樓另外一戶,住著兩位中國神父的房客遷出之後,我們便用那僅可容納十三人打坐的房間,開始舉辦第七次禪七。嗣後每年有四次,那就是五月下旬的國殤假期、七月初旬的國慶假期、十一月下旬的感恩節假期、十二月下旬的耶誕及新年假期。其間曾有三次連續打兩個七,到一九八六年底,已是第三十五次,由於佛殿兼作禪堂的空間不大,最多容納二十四個禪座位置,報名參加禪七的東西方人士卻越來越多,故於一九八七年春,我們遷入了現址,最多已可接受三十八位禪眾共同打七了。
時間好快,一轉眼,到本年感恩節的禪七,已滿五十次,每次禪七中的開示,也被陸續整理,編輯成書:
《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已由繼程法師譯成中文《佛心眾生心》,一九八二年出版。
《開悟的詩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一九八七年出版。
《信心銘講錄》(Faith in Mind),一九八七年出版。
《摩根灣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ay),一九八八年出版。
《寶鏡無境》(The Infinite Mirror),一九九○年出版。
《智慧劍》(The Sword of Wisdom),一九九一年出版。
《用扇接羽》(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一九九一年出版。
此外尚有一本書已經完成正在等待排版,另有兩本書已在著手編輯中,這些都是出於中、美、英的諸位熱心弟子的努力奉獻,對於將佛法推廣到英語社會,業已產生若干影響。
在第五十次禪七中,也頗有特色,第一是男眾人數超過女眾。第二是老參久修的禪眾多過新學,例如薛維格教授、約翰派克醫師(John Parker, MD)、邱克倫及他的夫人蘇珊均已習禪十幾二十多年。第三是共有三位禪眾,具備主領一地禪修的身分:
英國的約翰‧克魯克(John Crook),已在負責威爾斯的禪堂。
緬因州的邱‧克倫(Hugh Curran)正在負責摩根灣禪堂的經營。
冰島的衛史吞‧羅特維克森(Vesteinn Ludviksson),已發起成立了該國的坐禪會。
可見我到此時為止,雖在接引西方人出家這方面沒有成功,然把佛法傳給西方人並讓他們再傳下去的工作,我總算沒有白費了心血。
在我於美國接引及指導的弟子和學生之中,高級知識分子較多,除了正在攻讀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學生之外,有許多是工程師、醫師、教員、教授,其中有五位是在各大學專教佛學:于君方博士、史蒂文生博士、約翰‧克魯克博士、詹姆士‧哈利斯博士(James Harris)、邱‧克倫先生。他們目前分別任教於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布利斯朵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英國)、衛勃斯特大學(Webster University)、緬因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Ma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