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唯識學者,無不出身於禪宗,但是也有以弘揚唯識為其專職的人,可惜其中的若干位,已無傳記資料可考,現依據喻昧菴編《新續高僧傳四集》(以下略稱《新續僧傳》)以及《卍續藏》所收有關唯識著述的資料所見者,為主要根據,介紹如下:
魯菴普泰:不知何許人也,據他所作《八識規矩補註》的自序所述:「龍華金碧峯,圓通常無塵」,聽說他完成了該書,便「過舍索稿,板行之」。作序的年代是明武宗正德辛未年(西元一五一一年),書於大興隆官舍(註一)。他另外一部《百法明門論解》,自序亦於同一年作成。
又據王肯堂為通潤的《成唯識論集解》寫的序中說:「余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魯菴泰法師,行腳避雨止一人家簷下,聞其內說法聲,聽之則相宗也。亟入見,乃一翁為一嫗說。師遂拜請教,因留月餘,盡傳其學而去。疑翁嫗非凡人,蓋聖人應化而現者。」(註二)由於不知普泰的學統淵源,所以有此傳說。頗與無著菩薩夜請彌勒菩薩下來說法,誦出《十地經》,唯無著得近彌勒,餘人但得遙聞的傳說相似。不過在普泰的前述自序中,也提到了他曾目睹古人的好多關於唯識的註釋,只是:「為註之人,不書其名,往往皆抄錄之本。」可知他對唯識,早就留心。又知在他的時代,唯識學也能受到若干人的歡迎,所以當他的《八識規矩補註》一脫稿,便被人求去出版了。
紹覺廣承(西元?─一六○六─?年):他對明末唯識學的推動,有極大的功績,他的門下,出了好幾位重視唯識且有著述傳世的弟子。根據《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科》卷首,董漠策寫於清聖祖康熙戊午年(西元一六七八年)的序文說:「古杭紹覺老人,乃雲棲蓮大師嫡裔也。」(註三)可見他是雲棲袾宏(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的弟子。又在顧若群為《成唯識論自考錄》所寫的序中,也早提到:「於唯識之旨,當於此事,不得不推我雲棲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註四)此序寫於明莊烈帝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年),寫此序時,紹覺法師已「歿又幾二十年」(註五),可見紹覺歿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代(西元一六○八年之前)。除了靈源大惠,尚有新伊大真、辨音大基、玄箸、一相等人,都是他門下的唯識學者。他的第三代,則有《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的作者苕聖智素,此時已入清代。
另在《新續僧傳》卷六的「圓瓏傳」中,有如此的記載:「釋圓瓏,字大覺,姓鄭氏,武林人也,往來無極講席間,與雪浪、度門,相友善,而紹覺承,執弟子禮唯謹。……嘗讀《宗鏡》有省,與其徒承,手錄百卷,示鄰居士虞長孺曰:吾得掃除宗鏡堂,為壽師役,足可無憾。」(註六)
以此可知,廣承也是圓瓏的弟子,圓瓏又是無極的學生,無極(西元一三三三─一四○六年)是明初的高僧,常講《華嚴經》及《法華經》諸經。廣承又因其師囑其與師共錄《宗鏡錄》百卷,其師又與重視唯識的雪浪洪恩及度門正誨相友善,所以他之弘揚唯識,乃是意料中事了。
又在《新續僧傳》卷七「大惠傳」中提及:「時蓮居紹覺,從雲棲分席土橋,惠以白衣參叩,問《觀經》上品上生章,夙通頓發,慨然遂稟歸戒,詢及法要,覺為首舉臺相二宗,惠即銳心研習,多所詮解,覺深器之。」(註七)
從這段資料,得知廣承親近的大善知識,至少有兩位,一是雲棲袾宏,一是土橋圓瓏,他所教授弟子的,則以彌陀淨土及天臺、法相的三宗為範圍。
又從《卍續藏》六一冊收有《毘尼珍敬錄》一書二卷,據其卷首的序中敍述:「雲棲大師發天臺之隱,扶律輔教,為萬世規第,亟於《梵網》而未遑《四分》,……蓮居紹公,精徹臺宗,取《四分》,手自輯錄,以就茲篇,真妙補祖闕而善繼師志者。公往而其書塵襲已十餘年,近冢嗣新師,始托素師訂定。」(註八)此段文字不僅承認了廣承是雲棲的弟子,而且克紹箕裘,不但精於天臺,尤其長於四分律學。不過,他的《毘尼珍敬錄》,要待他的弟子新伊大真,請智旭素華代為訂定並作了戒相攝頌之後,始在教界流通。一如他的《成唯識論音義》,並未完稿,待其弟子辨音大基作疏之後,方能流通。
度門正誨(西元?─一五八九─?年):關於此人資料極少,從前舉《新續僧傳》的「圓瓏傳」所見,他是與雪浪洪恩同時,可能也曾往來於無極的講席。從其《八識規矩略說》的自序,劈頭便引《華嚴經》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而云:「移塵沙劫於食頃,布華藏於毛端」的思想看來,他與《華嚴經》、《楞嚴經》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又到唯識學:「自奘而後,亦有釋其文而明也者,顧非所明而明之,彌不明也。我朝正德間,有大法師泰公,起而明之,於是探玄之士,始有明其明者。」可知他對唯識的先輩古德,奘師之後,只推普泰。此序寫於萬曆己丑年(西元一五八九年),地點是在衡陽華藥山大藏閣。說明他曾駐錫湖南,但卻不知他是何許人氏。又從浙江檇李的一心居士朱衷純於萬曆癸巳年(西元一五九三年)所寫〈八識規矩略說跋〉中,見到如此敍述:「幸有度門禪師,戒景夜淨,空華曉揚,思風發于清襟,言泉流於玄吻,飲靈三藏,倫采群宗。」可知他既精於義學的思辨,又是一位戒行高潔的禪師。
真界幻居:根據王肯堂的記述,金陵攝山的素菴法師,有法嗣名幻齋,嘗講因明,是故紫柏大師令其為王肯堂等講解;又在紫柏大師弟子密藏禪師僧舍,見到幻居法師的《因明入正理論解》較幻齋所講者明晰(註九)。疑此二人,同出於素菴之門下,同時也曾親近紫柏大師。又從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的自跋中,自述其「嘗掩關閱《起信論疏》,至因明三支比量之說,若蚊蚋嚙巨石,毫無所入」。後於掛錫海虞的中峯,聽說有三懷座主在金陵瓦官寺,講因明,前往請益,又至燕山,親近玉菴座主,學因明論解(註一○)。
然於《新續僧傳》卷六,則有如下的記載:「真界字幻居,檇李人,亦來吳中,棲止南屏松壽堂,註解《金剛經》,視古今百家註無當旨者,獨會祖意而為之註,直指人心而不襲舊語。……註成,六夢居士序之,去隱西溪,無何端坐而化。」(註一一)
真界乃是一位禪者,故以自己的修證體驗來註《金剛經》,可惜此註未被收入藏經,他以閱《大乘起信論》至因明的方法論而發心研究因明,於西元一五八九年完成《因明入正理論解》,後來於西元一五九九年完成了:1.《大乘起信論纂註》二卷,2.《楞嚴經纂註》十卷,3.《物不遷論辯解》一卷(註一二)。可徵其非專以唯識為研究對象的學者。
高原明昱:此人事蹟不詳,但從被收於《卍續藏》的八種他所寫的唯識詮釋書,知道他是明末專志於研究法相及弘揚唯識的人,似乎他也很少與當時的諸大師來往,他的諸種著述的撰成,大概是在西元一六○○年至一六一二年之間,他與紹覺廣承、雲棲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同一時輩,故在他的《成唯識論俗詮》完成之後,雲棲大師也是捐資助刻者之一(註一三)。也許他的思想是以相宗為本位的緣故(註一四),當時諸師之中甚少有人於著述間提及此人,唯識學者之中,亦僅王肯堂的文字中見到明昱的名字,在明昱的作述之中,也絕無僅有地提及王肯堂,而此兩人在見解上仍大有出入(註一五)。有關明昱的事蹟,僅見於江寧寶林居士顧起元為《成唯識論俗詮》所寫的序中提到:「今何幸有高原昱公,開此線徑,使人人涉羊腸之詰曲,頑履康壯哉!公起自潼川,掛錫吳越,清跱絕俗,靈悟鮮倫。……以宇泰先生之請,詮釋此論。」(註一六)
《成唯識論俗詮》既成,自序則寫於「南屏松壽堂」,自稱為「西蜀輔慈沙門」。此書是由王肯堂請這位來自西蜀的義學僧,以一年的時間,在為「東禪」及「南屏」兩處的學者演講之下完成。而此「松壽堂」,也正是真界幻居於「吳中棲止」時的同一道場。《新續僧傳》「圓瓏傳」說:圓瓏始將《宗鏡錄》傳寫於吳,吳中士人多喜讀之,當時「妙峯並駐南屏,與筠泉蓮為友,皆遠嗣永明壽」。可徵吳中的松壽堂,是當時佛教界的緇素人文的薈萃之所,以《宗鏡錄》為研究的中心,而對唯識的興趣亦濃,廣承亦可能隨圓瓏到過南屏,明昱與當時的僧界,亦非沒有來往,然其《成唯識論俗詮》問世之際,請了八人寫序,竟無一位僧人與焉。居士中的王肯堂(西元?─一六一三─?年)、顧起元(西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年)、黃汝亨(西元一五五八─一六二六年)、吳用先等,均係名公巨卿。智旭是明末諸師中唯識的後起之秀,而且也是吳人,在其作述中,雖曾一度提到《成唯識論俗詮》的書名,卻未見其述及明昱的人名(註一七)。
達觀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自號紫柏,為明末四大師之一,在《新續僧傳》卷七,有其傳記,更早則有其私淑弟子角東陸符所撰的傳記,尤為詳細,作為《紫柏尊者別集》的附錄,被收於《卍續藏》一二七冊(註一八)。於其傳記中有關唯識法相的記述,僅得「因遊匡山,深究相宗精義」之句,那時他才二十多歲,已在開悟之後。
在王肯堂的作述中,則有三次提到紫柏大師與唯識法相的關係:
「余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註一九)
「余始聞唯識宗旨於紫柏大師,授以此論,命之熟究。」(註二○)
「余與董玄宰,侍紫柏大師於金陵之攝山中,日相與縱談無生,且謂枯坐默照為邪禪,非深汎教海不可。一日於素菴法師閣上,得一小梵冊,有喜色,手授余二人曰:『若欲深汎教海,則此其舟航維楫乎。』觀之則《因明入正理論》也。」(註二一)
紫柏大師以一位傑出的禪僧而重視義學,並著眼於唯識的存續問題,勸囑王肯堂等熟究《成唯識論》,又將因明喻為深汎教海的舟航。他自己也寫了一卷《八識規矩頌解》以及一篇短文〈唯識略解〉。他強調:「有志於出世而荷擔道法,若性、若相、若禪宗,敢不竭誠而留神(於唯識之書)哉?」(註二二)
一雨通潤(西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四年):他是明末佛教界的一位極有成就的著述家,他的著作被收入《卍續藏》的即有六種(註二三),無怪乎他對唯識的研究,極富心得。當王肯堂聽說有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於焦山,遍檢《大藏經》,將譯《成唯識論》,便派人迎到家裡,二師雖先後到了,對於為作補疏的事,則皆以非得請到通潤不可(註二四)。通潤的唯識學淵,則如王肯堂為《成唯識論集解》作的序中所說:「雪浪法師,即魯菴之孫也,緣督又雪浪之孫,而一雨、巢松二師,皆得法雪浪,稱高弟子。」(註二五)
通潤是雪浪的法子,亦即是魯菴的法重孫。雪浪洪恩在明末佛教界,也是一大重鎮,《新續僧傳》卷七有他的傳。智旭推崇他,稱為「慈恩再來」(註二六)。雖然他的著述被流傳下來的不多(註二七),可是明昱及智旭註的《相宗八要》的八種唯識學的書目,即是根據洪恩從《大藏經》之中錄出來的(註二八)。從《新續僧傳》所載,得知洪恩是無極的學生,善講《楞嚴經》、《圓覺經》、《般若經》。因而他的法子通潤,也自號為「二楞菴」,註釋《楞嚴經》及《楞伽經》二經,以會通性相二宗為其宗旨(註二九)。
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也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二卷,收於《憨山大師夢遊集》卷五三及五四,是故他的傳記資料,是明末諸高僧中最完整的一位。他是一位有修有證的禪僧,也是一位重視義學並且有大量著述傳世的高僧。他與相宗有關的著述,僅是《百法明門論論義》及《八識規矩通說》的兩種各一卷,被收入《卍續藏》。他曾親近無極、徧融諸師,與雪浪、紫柏為善友。在其生命史上與相宗最有關的,是三十三歲那年,進入彌勒樓閣的一個夢境,由於在夢中聽了彌勒菩薩對他講說:「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註三○)。他從自內證的經驗,明瞭智與識的不同,他的相宗註釋,也是以修行的立場為其著眼。例如他在《八識規矩通說》的文前說:此書乃「為一大藏教之關鑰,不唯講者不明,難通教綱;即參禪之士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滅頭數」(註三一)。同書之末,他又表明:「正要因此(《通說》使學者)悟心,不是專為分別名相也。」在他晚年,手批其侍者廣益纂釋的《百法明門論》時,則說:「此《百法論》,以門稱者,乃入大乘之門,是知此乃性相二宗之關要。凡義學者,未有不明此法而能窮諸法門者。」(註三二)可知他將《百法明門論》,視為性相二宗的入門書,而鼓勵弟子們學習它。據《憨山老人自序年
譜實錄》稱,他到七十一歲那年,因澹居鎧公請益性相宗旨,故依《大乘起信論》會通《百法明門論》。他本身不是相宗的唯識學者,已很明顯。
靈源大惠(西元一五六四─一六三六年):他自稱「蓮居弟子」,足徵他對於紹覺廣承的崇敬。《新續僧傳》卷七有他的傳記,同時在「雲棲學菩薩戒弟子大璸顧若群」為《成唯識論自考錄》所寫的序中,也作了若干介紹:「當今此(唯識學的)事,不得不推我雲棲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靈源師者,勾餘仕族,年未壯室,以優婆塞,入土橋覺師二十年,口輪未嘗停傳,源師入耳輒服膺,朝往暮歸,中途尋記其師說,必如昔人所稱,分水瀉瓶而後已,故師歿又幾二十年,其所傳習,獨不謬海昌。」(註三三)
又從《新續僧傳》得知,大惠出家時,已五十七歲,然在白衣時代,早以士人身分,親近善知識,受廣承的十年薰沐之後,嘗於京師慈慧寺聞其開山比丘愚菴真貴(註三四),講八識標指,而微參疑義,為貴師歎服,故邀其登座,以未出家為辭,強而後可,所宣皆是蓮居廣承的唯識宗旨。出家受具之後,因辨音大基於補充廣承的《唯識論》之疏,刻板於海昌,大惠以為廣承之旨頗有出入,故撰《成唯識論自考錄》問世,同門的新伊、古德、金臺、元著(玄箸)諸上座,讀畢咸謂:「儼若蓮居講筵未散。」(註三五)
新伊大真(西元一五八○─一六五○年):與大惠同門。《新續僧傳》未見其傳。可是在他同時代的蕅益智旭,對他備極稱讚,見於《靈峯宗論》卷八者,特為大真所寫的文章,即有五篇之多,說他年十五從廣承為沙彌,習師所演教法,夜以繼日,慈恩、臺岳宗旨,每多遊刃而心益虛。後繼廣承而主持蓮居,力弘紹覺之道,著《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兼授金剛寶戒,而教觀並舉(註三六)。他不是專弘唯識的學者,卻是唯識學的探究者。又如旭師所說:「師童真入道,為紹公長子,性相二宗,無不克受其傳,服習毘尼,視紹公尤加焉。」(註三七)可知大真對於天臺智顗、南嶽慧思、唯識、戒律,都很重視。他著有一部《成唯識論遺音合響》,此書是繼紹覺廣承未完的《成唯識論音義》而作,正如大基之作《海昌疏》。只是《海昌疏》遭大惠批評而未流傳,《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則由大真的弟子苕聖智素,合輯為《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現被收入《卍續藏》。智旭給大真的《成唯識論遺音合響》,所作評價極高:「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述為《音義》八卷,一簣功虧,忽爾西邁。於是及門高士,各出手眼,如辨音基師之《疏》,靈源惠師之《自考錄》,亦既各竭精思、殫才力,然皆升堂有餘,入室未足,故使學斯宗者,無由詣極。惟新伊真師,紹師嫡胤,執侍最久,聞熏獨深,遂能繼志述事。」(註三八)
紹師門下,人才出眾,有成就於唯識學的而著書立說者,即有三家,智旭獨推大真方為「嫡胤」、為「長子」,其中原因,乃在於思想的投契吧!
王肯堂(西元?─一六一三─?年):自號樵子,字宇泰,江蘇人,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進士,倭寇犯朝鮮,疏陳十議,後被任命為南京行人司副,最後任官為福建參政。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所競傳。晚年學佛,而「以老病一措大,博得會禪之名滿天下(註三九)」。以學禪而與董玄宰等,同去親近紫柏大師,也許紫柏大師見他博學深思,精於考究分析,故以熟究唯識相囑。因此使他接觸到了當時有志於唯識的諸僧,例如:
聞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於焦山,研究《成唯識論》,肯堂移書招之,二師各出其所標點之本,互相印證,肯堂因此而有正誤標義之刻,四方學者,始有此論可究。
聞王太吉言,相宗之精,無如高原法師者,《觀所緣緣論釋》,曾不可以句,而師釋之如指諸掌,則其他可知也。時東禪無主,肯堂遂虛席以延明昱,師率徒至,因囑其略釋此論(註四○)。
由巢松及緣督二師之推薦,肯堂遣使迎一雨通潤,令為《成唯識論》作補疏,通潤當時雖以他事所羈未至,約十年後,緣督已作古,肯堂亦老病,通潤的《成唯識論集解》則完成了(註四一)。
因親近紫柏大師囑究因明而向幻齋學。訪真可的弟子密藏道開,得幻居的因明解。又在何矩所齋中,讀到師子窩鎮澄法師(註四二)的因明解。又於萬曆壬子年(西元一二一六年)夏,請蘊璞法師結制於肯堂的拙隱園中,撰出因明解(註四三)。
他由於紫柏大師囑其留神唯識及因明,所以認識了雪浪及紫柏兩系的唯識學者,也促成了明昱、通潤、蘊璞等人,寫出了唯識及因明的註釋。最後,因他自己無法全部認同諸師的論點(註四四),故於西元一六一二及一六一三年,完成了《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及《成唯識論證義》二書。
虛中廣益:他是憨山大師晚年的弟子,教以研究唯識的下手處,後來稟承大師的指示,作成《八識規矩纂釋》及《百法明門論纂釋》兩書,均經大師手批,當時(西元一六二二年)大師已是七十七歲。於德清的《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中見到,在他六十七歲,為弟子講《大乘起信論》及《八識規矩頌》,述《百法直解》。七十四歲又講一次《成唯識論》,可知廣益是他晚年的弟子,到了七十五歲那年春天,廣益請大師重述《大乘起信論直解》及《圓覺經直解》等(註四五)。在嶺南仲安劉起相為《百法明門論纂釋》所寫的序文中,也說廣益是德清座下諸上足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註四六)。
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早年的智旭,人稱素華,年齡小於廣益,依德清的弟子雪嶺為剃度師,被公認為明末四大師之中的最後一位,他的傳記資料相當豐富,見於《靈峯宗論》的「八不道人傳」,《新續僧傳》的「智旭傳」,弘一演音編訂的「蕅益大師年譜」等,均係研究智旭傳記的資料(註四七)。
智旭是明末佛教界的大著作家,總計寫了五十一種不同的專作,共有二百二十八卷之多。有關唯識的著述,即達九種十八卷,堪與另一位明末的唯識大家高原明昱,互為伯仲。明昱除了專攻唯識之外,並未留下任何其他著作,智旭則縱橫教海,舉凡天臺、法相、戒律、淨土、禪,無不著有專書遺世。所以他也不是以繼承相宗的陳說為宗旨的人,倒是站在性宗的立場,作著會相歸性、相為性用的努力。從智旭的作述之中,提到明末唯識研究的動態者,有三處:
〈重刻成唯識論自考錄序〉有云:「萬曆初年,紫柏大師接寂音之道,盛讚此宗。爰有《俗詮》、《證義》、《集解》諸書,而紹法師《音義》為長,《音義》未全故不流通,基法主續補成《疏》,亦頗簡要,惠法主謂《疏》多譌,復出此
《自考錄》。」(註四八)
〈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序〉有云:「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註四九)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緣起〉有云:「紹覺法師為之『音義』,一雨法師為之『集解』,宇泰居士為之『證義』,無不殫精竭思,極深研幾。然教道已明,觀道未顯。嗣有新伊法師為之『合響』,力陳五觀,冠罩諸家。」(註五○)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智旭對於明末唯識學者的態度,推重紹覺廣承的一系。由紫柏大師的盛讚,引出《成唯識論俗詮》、《成唯識論證義》、《成唯識論集解》,此三人均在廣承的系統之外,唯有廣承的《成唯識論音義》、大惠的《成唯識論自考錄》、大真的《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受到智旭的稱讚。特別是大真的《成唯識論遺音合響》,以「觀道」為主眼,所以歎為「冠罩諸家」。而智旭自己之註解唯識,「不敢更衍繁文,祇圖直明心觀」,他以重視實修的立場,他不作繁複的徵引,也不細究外道的計執,使讀者將文字句句消歸自己。他雖是模擬天臺家註釋經論,而稱「觀心」,但他「以此論成立唯識道理,即是觀心法門,不同法華別立觀心釋也」(註五一)。故將他的註解稱為《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在所有的唯識註釋書中,這是非常特別的一部。
智旭另有《相宗八要直解》,書目的選定,是根據雪浪洪恩所指定,已如前述。「直解」二字,則是受了憨山德清的影響。德清嘗有《百法直解》(註五二)及《八識規矩直解》,然未見入藏,推想在智旭時代,已只知其名而未見其書,所以因襲「直解」,否則他豈敢採用與德清著作的同一書名?
王夫之(西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農,號船山,湖南衡陽人,崇禎年間(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三年)舉於鄉,瞿式耜薦於桂王,授行人,不久歸居衡陽之石船山。先後有張獻忠及吳三桂,逼請其出山,均未赴命。夫之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註五三)為堂奧,尤其服膺張載而力闢陽明致良知之說。他的佛學淵源不明,然而筆者最近由一位韓國的法師處,見到一冊木刻本的《相宗絡索》題謂「衡陽王夫之譔」,計二十五紙,共列二十九個唯識學的名相,作簡明介紹,未雜性相融會的觀念,亦未見以儒釋佛或以佛釋儒的論調。其目的顯然僅在明瞭相宗的名相,未有其他企圖。
綜合以上的分析介紹,對於明末諸家的唯識學者,及其系統關係,可以列表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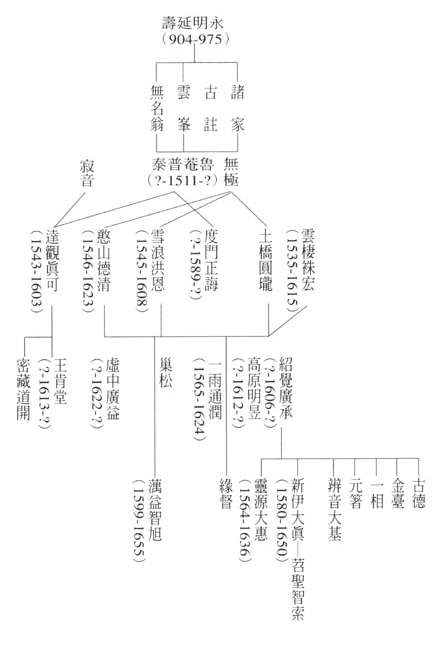

註解
《卍續藏》九八.五一三頁。《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上。《卍續藏》八二.七○九頁。《卍續藏》八二.九一─九二頁。同上九二頁。《新續高僧傳第四集》(以下略稱《新續僧傳》)卷六.九─一○頁。此書係為喻昧菴編,臺灣瑠璃經房一九六七年重版。同上卷七.六頁。《卍續藏》六一.五五九頁上。
《卍續藏》八九.一○五頁上。《卍續藏》八七.一○三頁下。《新續僧傳》卷六,「圓瓏傳」。
現被收於《卍續藏》七一冊。
現被收於《卍續藏》九○冊。
現被收於《卍續藏》九七冊。《卍續藏》八一.六頁上。《成唯識論俗詮》自序云:「成立宗因,精研相性,導引多方,終歸唯識,漸亡百計,始悟玄猷,即彰五位,使知趨進。」(《卍續藏》八一.六頁上)
王肯堂序《成唯識論俗詮》(《卍續藏》八一.三頁)。
明昱自序《成唯識論俗詮》(《卍續藏》八一.七頁上)。
《成唯識論證義》王肯堂自序云:「《俗詮》之作,吾嘗預商訂焉,及其刻,則從與不從,蓋參半焉。」(《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下)《卍續藏》八一.一頁上。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首卷(《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
〈重刻成唯識論自考錄序〉(《靈峯宗論》卷六之三)。〈別集附錄〉撰於紫柏大師寂後三十二年,即是西元一六三五年。
《新續僧傳》撰於西元一五二三年。《成唯識論集解》序(《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上)。《成唯識論俗詮》序(《卍續藏》八一.二頁下)。《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自序(《卍續藏》八七.一○五頁)。〈唯識略解〉(《卍續藏》九八.五八一頁上)。
《圓覺經近釋》六卷(《卍續藏》一六冊)。
《楞嚴經合轍》十卷(《卍續藏》二二冊)。
《楞伽經合轍》八卷(《卍續藏》二六冊)。
《法華經大竅》八卷(《卍續藏》五○冊)。
《起信論續疏》二卷(《卍續藏》七二冊)。
《成唯識論集解》十卷(《卍續藏》八一冊)。王肯堂作《成唯識論集解》序(《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下)。《卍續藏》八一.三○四頁上。《靈峯宗論》卷五之三,二四頁。《卍續藏》僅收洪恩的著述《般若心經註》一種(《卍續藏》四一冊)。
玉溪菩提菴聖行〈敍高原大師相宗八要解〉云:「余因憶昔白下雪浪恩公,演說宗教,特從《大藏》中錄出八種示人。」(《卍續藏》九八.六八五頁上)見《卍續藏》一六冊及三六冊。《夢遊集》卷五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卷下(《卍續藏》一二七.九五八頁上)。《卍續藏》九八.五八三頁上。《卍續藏》七六.八六○頁上。《卍續藏》八二.九二頁上。真貴作有《仁王經科疏科文》、《仁王經科疏懸談》等,收於《卍續藏》九四冊,自稱為「賜紫玉環比丘蜀東普真實」,又稱「嗣賢首宗第二十五代」(《卍續藏》九四.八五七頁)。另著有《楞伽經》、《唯識論》、《藥師經》、《圓覺經》等註(《卍續藏》九四.一○七三頁)。《新續僧傳》卷七,六頁B。《靈峯宗論》卷八之一。《靈峯宗論》卷八之二。智旭著〈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序〉(《靈峯宗論》卷六之三)。
《成唯識論證義》自序(《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下)。以上兩則取自《成唯識論俗詮》之王肯堂序(《卍續藏》八一.二頁下─三頁上)。《成唯識論集解》之王肯堂序。《新續僧傳》卷七有「鎮澄傳」,曾與憨山、妙峯結隱五臺,有《因明入正理論》、《大乘起信論》、《永嘉集》諸解行於世,萬曆丁巳(酉元一六一七年)寂,世壽七十有一。《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王自序(《卍續藏》八七.一○五頁)。《成唯識論證義》自序云:「《俗詮》之作,吾嘗預商訂焉,及其刻,則從與不從,蓋參半也。《集解》之見,與吾合處為多,而不合處亦時有之。吾見之未定者,不敢不捨己而從,而吾見之已定者,亦不敢以苟同也,此《證義》之所以刻也。」(《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下)《夢遊集》卷五四(《卍續藏》一二七冊)。《卍續藏》七六.八六○頁下。參考聖嚴著日文本《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一三二─一四○頁。《靈峯宗論》卷六之三。見本節註三八。
《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緣起》(《卍續藏》八二.三九三─四頁)。
《夢遊集》卷五四,有〈述百法直解〉(《卍續藏》一二七冊)。
憨山老人手批《百法明門論纂釋》,有「則取直解」句(《卍續藏》七六.八六○頁上)。
憨山老人手批《八識規矩頌纂釋》,有「參以直解」句(《卍續藏》九八.五九三頁上)。周敦頤、程頤、程灝、張載、朱熹等五人,合稱為宋之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