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我是狼山的孤僧
從狼山的殿宇名稱看,例如關神廟、靈官殿、江神殿、文昌殿等,乃與地方性的香火道場同一類型,仍介乎民間信仰與佛教信仰之間,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年),張季直狀元,請太虛大師到狼山講〈普門品〉,有意整頓狼山道場,擬改子孫寺院為十方禪林而未果,大陸被統治四十年後,狼山七個房頭,僅存其二,而已合為一寺,狼山的老僧,尚健在人世者,只得育枚、自覺、宗律、俊德、演誠等五人,全山現住五十來位僧眾,其中多半是來自南通地區的原有各寺,如今集中於狼山一寺,加上十來位文革以後剃度的青年比丘共住,狼山實質上業已不見子孫寺院的型態。
狼山腳下,舊日的砲臺街數十家香燭店,已全部拆除,並且開鑿了一條明河,沿河新栽的桃花成行,正值盛開季節,狼山已是公園的形式,大門即是園林部門所管理。購票上山的人,每天約兩至三萬人,其中是為進香祈福的,不足十分之一,昔年上山的人是為燒香,目前上山的人多為旅遊,大聖殿上仍是擠得只見人頭鑽動,多半卻是為看熱鬧。實際上,這像是個「沒有煙囪的工廠」,不能算是佛教的聖地和弘揚佛法的道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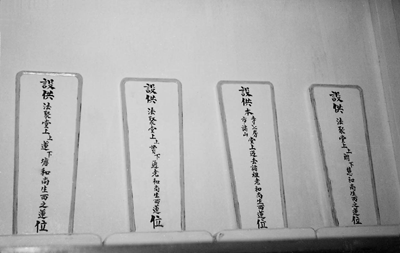
▲狼山往生願堂上列四牌位,其中三個都是來自我法眾堂上。
因此,我在四十多年來,雖然經常魂繫夢縈地懷念著曾在狼山出家的殊勝因緣,這趟回到狼山,竟無回到老家的感受。我住過的法聚庵,已非道場,法聚庵的五代老僧,均已作古,較我略晚出家的徒弟清華,已現俗相。如果我還是狼山僧,則已無祖庵可棲,向上無師可依,向下無徒為繼,真是一介孤僧!
我逐級走在狼山的登山道上,越發覺得自己是在觀光客的人潮中,孤獨地夢遊。
到了山頂,我被引至供著觀音像的偏殿,發現觀音像後供著上中下三排黃紙牌位,我不等他們說明,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立即老淚縱橫地頂禮三拜,抬頭看見中排四個牌位,竟有三個是我法聚庵的老和尚,他們是我師祖貫通、師公朗慧、師父蓮塘。還有更老的兩代,也許去世得更早,所以未見他們的牌位。
狼山師長對我未有多少培植,但是由於他們能夠度我出家,並且肯送我去佛學院,始有我的今日,那已經是大成就、大栽培和大恩德了。可是我這次回山,只有默對三個牌位念佛,連說一句謝謝的機會都沒有了。

▲與狼山方丈(昔年靜安佛學院的教務主任)育枚長老。
這兒,是我走上佛學之途的起步之處,現在,那幾位曾經攙我學步的老和尚在那裡呢?據說,貫通老人已經還俗,在工廠做工三十多年,最後回到狼山去世;朗慧老人在大陸被統治後不久,便以勾結日軍等罪名,判刑十七年,被送新疆勞改,結果死於該地;蓮塘老人被找回狼山時,已經老病,到去(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以哮喘病併發症捨壽。
山頂下來,在法乳堂過午,菜式豐富可口。住持育枚長老,今(一九八八)年七十九歲,患著嚴重的腳病,已是寸步難行,好在耳聰目明,憶舊如新,聲音宏亮,氣宇豁達。本在醫院療養,見我到訪,歡喜非常。自覺長老原是四賢祠的當家,四十多年未見,對我印象模糊,卻親筆寫了一副對聯送我,筆跡蒼勁,頗有功力,可惜落款時,將我的名字誤寫成「聖然」。宗律是育枚老的徒孫,也有七十來歲,俊德、演誠,是我同輩而較我略長,亦都六十開外,他們三人,只能記起我在狼山時代的一些片段。已結婚生子的清華,始終跟我身邊,心情極其凝重,我在山頂三位老和尚的牌位之前,流過眼淚之後,早已恢復平靜,而且談笑自若,他卻老像是把我當作從海外回來奔喪的長輩接待。
我在現已改名為「紫琅圓」素菜館的法聚庵,巡禮了一遍,房舍全部都在,只是缺少了五位老僧,也撤除了所有的佛像。庭苑中不再有花木扶疏的盆景,也少了儲蓄雨水用的數十口大缸,曾是我習誦的老佛堂,改成了販賣部;曾是我朝暮課誦的新佛堂,已改成第二食堂,稱為「北餐廳」;原來的大客廳及住持寮,現在是大餐廳;曾是我臥室的小廂房,門窗關閉,闃無人影;我曾經蒔花、種菜、澆水、除草的後苑,蔓草叢生,一片零亂。我一面參觀,一面心痛如絞。為什麼昔日的僧院,變成了今日的餐館?跨出門外,想到門側原有一座法聚庵的祖師塔,察看之下,已經不在。只是法聚庵前的幾棵老銀杏,好像別來無恙。我問清華,他憂戚地回答:「銀杏少了一棵,祖塔已被拆除。」
到此,我的心念,反而轉了方向。佛陀不是早就說過的嗎?「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狼山的道場,從無而有,從有而無,已歷劫數次。歷史的展延,或有相似的軌跡可循,既然諸行無常,我們就不可能遇見完全相同的事物,也不可能回頭走上完全相同的路。只要我們自身時時腳踏實地,全力以赴就好。祖師開創道場,未必是為了後人給他起塔,整個的三千大千世界,都逃不出成住壞空的四大過程,何況是祖廟及祖塔。問題是在有沒有人能在破壞了的廢墟之中,再把它們重建起來?不僅要重建,而且要建得比往昔更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