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轉眼四十年
陳慧劍
朝元禁足,風景奇異
聖嚴法師到了朝元寺,起初是「禁足」,每日在寺方供應的閣樓上拜懺;先是「彌陀懺」,後來是「大悲懺」,一天兩堂。剩餘的時間,便是拜佛,晚間打坐,好像與「佛典」脫離了關係。在這段期間,身心非常安定。
不久,臺北的書運到,有幾十箱,自己便動手將書從樓下一箱箱往自己的小樓上搬,這些書,包括「佛學、文學、史學」等等重要典籍,也是他安身立命之所繫。
以一個生而弱質的他而言,每箱二十多公斤重的書,幾乎是不堪負荷的,但是寺中沒有人可供協助,只有自己費盡所有力氣來搬。他一箱箱地彷彿螞蟻搬家,忽然間,彷彿「失落」了什麼,自問:「誰在搬書?」誰在搬呢?沒有誰在搬啊?好像搬書的人消失了一般,自己也不見了;可是一箱箱的書都上了樓,也擺得好好的。這才如夢初醒的驚異起來。其實,已經幾個小時過去了。這一個謎成為他修道生活中第二次奇異的經驗。

▲一九六三年聖嚴法師於高雄美濃朝元寺掩關,入山相送者,前排右起:張少齊長者、能淨長老、作者、明常長老、南亭長老、月基長老、妙然法師、煮雲法師。後排中為當家師慧定、善定比丘尼。
是不是通過拜懺、業障消了,心靈清淨了,有佛菩薩護持呢?這一答案至今還無法解答。但是他已決定──真正的閉關時間應該到了。
他從臺北南下,經過多方周折到了美濃,本來的目的就是閉關修道與讀經,可是,朝元寺那裡有多餘的房子為一位雲水僧來護持「閉關」呢?而自己又是初還僧服,也沒有信徒護持他「閉關」。自己退役後的一點錢,又為道友急難付出去了,實在沒有能力來建造關房。
過了一個月,臺北華嚴蓮社智光長老向他皈依弟子張居士提到有一位精進佛道的後輩,需要護持,這位居士便專程到美濃山中來探望聖嚴法師,慷慨地問到建造一間關房需要多少錢?他願意供養。關房的事經過一番估價並與朝元寺磋商,定案之後,張居士與朝元寺共同供養了這間關房,在不到一個月之後完成,因此,聖嚴法師便在諸多因緣湊合之下,也可以說是龍天護法吧──順利地進了關房。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這位青年法師在風光幽靜的美濃朝元寺入關,雖然也有個簡單的閉關儀式,但觀禮者寥寥無幾。這一年,他是三十四歲。
在關房裡,他排定了功課,仍以拜懺為主,下午三點以後,以兩個小時來看經。但是「怎樣看,先看那一部經」,卻茫無頭緒。不過他想到曾經看過印順法師一種著作中,曾寫到「阿含」是佛家思想的源頭,所以,他便決定由「阿含」入手。他排定了閱讀阿含的程序──從《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到《長一阿含經》。每天以三個小時埋頭於阿含,一邊看一邊做筆記。其他時間仍舊拜懺、打坐。這位初步埋首於經藏的法師,非常歡喜打坐。

▲聖嚴法師於關房中。
他未進關房之前,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是他的禪坐專用時間,但他打坐的方法非常奇特,既不修觀也不參禪,更不念佛,也就是說上述佛家修定大法,對他而言竟然都不契機,他的「打坐」是諸法之外的「純打坐」,不加任何「禪觀」,他也自知,這是個人的創作。
他記起,在修道的歷程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轉捩點是在二十八歲那年,虛雲老和尚的法裔──基隆大覺寺的靈源老和尚的一頓拶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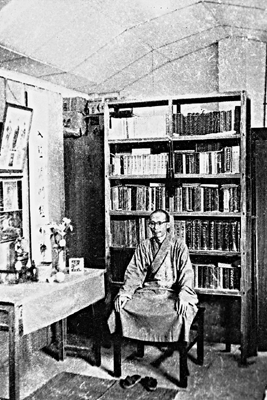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聖嚴法師於關房前留影。
當時,他還在國防部通訊部隊服役,住在新店,他的寢室正面對「廣明岩」上巨型的「阿彌陀佛」石像。他每天對著二公里外的阿彌陀佛禮拜,而當時「心情苦悶」也是原因之一。解決不了的問題太多太多。之後不久,他去高雄五福四路佛教堂拜訪月基法師,那天晚上那個看起來累累贅贅、迷迷糊糊的靈源老和尚,也從基隆到這作客,晚間,這一僧一俗(他仍著軍服)被派在一間通鋪上同單而眠,頭上掛一頂大蚊帳。可是,這位和布袋和尚一樣身材的老和尚並沒有睡覺,他挺著大肚子打坐,看到他打坐,尚是軍人身分的聖嚴法師(張採薇居士)也只有忍睡陪坐。
坐了不久,年輕人就忍不住,說自己多苦惱、多不安,有許許多多問題纏著。靈源老和尚說:「你可以問,你可以問……」、「喔喔,還有嗎?你還有嗎?……」老和尚講的好像是寧波話,令人混淆不清。「還有嗎?還有嗎?」一連串「還有嗎?」,就是不告訴答案。突然間他伸出手掌,拍地一聲打在床沿木板上,幾幾乎床都要震了起來。「你那來那麼多問題!擺下來睡吧,我要睡了!」
就這樣被他一陣捶打,聖嚴法師一籮筐的問題,竟然煙消雲散,被打掉了。
從此以後,他的心便穩定下來。他深刻地體會,「修行」對一個棄俗的出家人太重要了。因此,「打坐」在日後,甚至一直到今天,依然是聖嚴法師維護佛法生命的道糧。
正式寫書,是從閉關後半年才算開始,雖然,在朝元寺隱居禁足一年十個月之中,也陸續定稿幾類「認識佛教」粗淺的書,但是一經閉關、讀經以後,靈思便如潮水湧來,因此,他的第一類「傳道書」──《正信的佛教》便在一九六四年完成,一九六五年五月問世。
六載閉關,天地宏開
聖嚴法師讀完「四阿含」,寫成《正信的佛教》,接著是埋頭於「律藏」,當時凡《大正藏》中所能見到的律典,無一遺漏,因此,他對佛教僧團的制度、生活、戒相、瞭解得十分清楚而細密,他一邊讀一邊寫,在古人語焉不詳處,引起自己「解釋律典」的弘願,經過十個月時間,又完成了著名的《戒律學綱要》一書。
但是他的閉關生活依然是平淡寧靜的,每日上午拜懺,下午看經、寫作,晚間打坐。不過後來改為上午讀經、下午寫作、晚間仍舊打坐。這是「定慧雙修」的閉關生活。在關中到一九六六年初,因為眼疾需要治療,迫不得已,在同一年八月七日方便出關,到高雄看病,因而受到高雄壽山寺星雲法師之約,在壽山佛學院講授《比較宗教學》與《印度佛教史》;前後十個月,一面講學、一面寫作,在美濃與高雄之間往返奔波,終於因為這種生活與自己閉關修道大相逕庭,加上都市生活送往迎來,到次年六月十日,回到美濃,再度入關。這次入關,驚動了佛教界前輩印順導師、白聖長老、剃度師東初上人,以及同流道友紛紛來山相勉,在一個比丘僧來說,「閉關」不能不說是「終身大事」,何況他是「二度入關」,是鐵石心腸,投入「了生死、斷煩惱」行列的。想不到東初長老,竟然命他出關,到東京去留學。這是聖嚴法師日後暫別山居生活出國留學的契機。
所謂「山中無歲月,寒盡不知年」;聖嚴法師在山中,「日中一食」──由朝元寺常住供養,讀經與寫作在時間上有時互相更替,唯有晚間打坐,從未變動,「身在禪中不見禪」,不管在知識與境界兩方面,都已另見天地了。

▲聖嚴法師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再度掩關時,高雄美濃朝元寺能淨長老率該寺住眾送關。
在這整個閉關、行解雙運的日子裡,聖嚴法師究竟修什麼、證什麼?
他修的是「心中無繫念」的「無念法」。心中無念,何其困難?但是聖嚴法師在這一特殊的方法上,找到了「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的「本來無一物」的一絲不掛禪。他沒有師承、未經啟迪,用這一「離念、無念」、「非觀非禪不思議法」,開闢了另一片修行空間,若干年後,他為美濃修道方法,訂名為「疑似曹洞默照禪」。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因受臺北善導寺住持悟一法師邀約主持「佛教文化講座」而出關。
他總結美濃的閉關成果:
所有的修行方法除了「九十天的般舟三昧」之外,其他的有關佛家禪定(六祖禪、天臺止觀、念佛三昧)都試煉了,並且決定了寧願作為一位宗教家、一個老比丘,雖然自己修的不是中國正宗「禪」,但是他遍讀一切禪修的典籍,也選擇了日後教禪的路。
在經藏上,也選讀、精讀全部佛典中重要的經論,包括般若、華嚴、涅槃、楞嚴、法華、大智度論……。其中尤以「阿含、般若」最為得力,凡是重要的經論都已做了一番浸禮。
由於在關中受到道友楊白衣、張曼濤居士傳來日本佛學研究的資訊與日文佛學著作的供應,通過閉關後期的日文佛典的自修,對日文著述已培養出閱讀能力,這對以後到日本留學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改變了中國佛教夜郎自大、坐井觀天的落後觀念。當時又接觸到外道對佛教的批判性挑戰,於是益加動念怎樣到日本從事更精深的佛教思想研究。
聖嚴法師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到美濃閉門讀經,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出關弘法,前後計達六年三個月零八天。法師的初期作品,在閉關中大量湧現,最重要的代表著作,當推《戒律學綱要》之問世;這本書透過一般論文作法,來演繹佛家戒律的義理,極受海內外佛教高級知識分子之注意;佛律之在中國學術化,同時也足為僧俗共讀,這是第一部值得珍視的書。

▲一九六八年聖嚴法師在臺北市善導寺的彌陀殿專題演講。
聖嚴法師出關後,善導寺講經一年中,一面進修日語,於是經過申請及準備,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終於獲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的入學許可。
負笈東瀛,浸沈學海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他從臺北到東京,踏上了留學的征程。這是他閉關期間受到剃度師父東初老人的鼓勵,尤其是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張曼濤居士的勸請,並在閉關中閱讀了許多關於日本佛教的著作,發現日本佛教在學術研究方面有輝煌的成就,儼然已執世界之牛耳。對研究資料的整理提供,再沒有其他國家可比。
而國內的佛教教育普遍的低落,僧眾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視。為了提高佛教學術的地位,因此發願到日本留學深造。雖然此時他已三十九歲,而且從未受過中等及高等教育,到達日本,進入日蓮宗創辦的立正大學,便直接由碩士課程開始攻讀。
兩年之後,完成碩士學位,回到臺灣,同時把日文的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翻成中文,交給《海潮音》雜誌連載,東初長老希望他回來之後,就不要再去讀書,但是他的指導教授,當時立正大學校長坂本幸男博士,認為他的程度和努力的方向,最好能繼續完成博士學位才有意義。因此,雖然許多國內僧俗大力勸阻,並且斷絕經濟後援,但他仍然再度赴日,繼續博士課程。
一開始,他準備博士論文,以明末的蕅益大師為中心,這與碩士論文有關,都屬於天臺系統。而從慧思到明末的階段,所有天臺的問題,幾乎都被人家研究過了,只有這個論題未被開發。
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這四年過程中,他除了攻讀學分外,所有時間都在東京各大學圖書館瀏覽。並利用寒暑假期,去訪問道場,實際去參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動。有傳統式禪宗的禪七和密宗的加行,也有各新興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動。不但瞭解到日本在學術方面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在宗教活動上,不論是傳統的佛教方式,或新興宗教的活動,也值得借鏡。比如他接觸到臨濟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長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及總持寺派和黃檗宗派的傳統禪,還有龍澤寺派新興的禪。
又接觸到天臺宗傳統的比叡山派的修行者,新興的孝道教團,還有傳統的淨土宗大德寺派和日本新淨土宗東本願寺、西本願寺派;傳統密宗的高野山派、成田山派;日本宗教的傳統日蓮宗身延山派和新興的日蓮正宗,立正佼成會、靈友會、國柱會等。
他接觸到這些宗派的領導人和年輕一代優秀的人才,而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並接受各宗派的邀請和招待,遊歷各地。除四國之外,南至沖繩,北至北海道,處處都曾有他的足跡。因此,得以見到日本從上到下全面深入的普遍的佛教現況。
在學術界,當他撰寫論文期間,拜訪過東京、京都有關天臺學及中國佛教的專家學者,同時參加了下列學術團體的活動:第一,「印度學佛教學會」;第二,「道教學會」;第三,「西藏學會」;第四,「日本佛教學會」;第五,「日蓮宗學會」;並提出論文,在會議上發表。由於學術會議是由南到北在各大學輪流召開。因此,他接觸到日本全國的有關學者,因他對東京的學術環境最為熟悉,並且東京是日本人文薈萃之地,因此,他也有機會接觸到世界性的學術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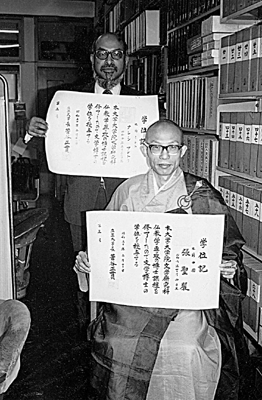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聖嚴法師與一位印度同學於取得博士學位證書後合影。
他的博士課程進行至第二年,指導教授坂本博士去世,生活費用也告罄。但他記取坂本教授的話:「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無道心。」同時,他記取東初上人的訓示:「願為宗教家,不為宗教學者。」內心默默祈求觀音菩薩加被。後來,他得到兩位指導教授:一位是印度學的權威,金倉圓照博士;一位是中國佛教史學權威,野村耀昌博士。他們看過他寫作論文的計畫和蒐集的資料之後,都表示十分歡喜,支持與鼓勵他繼續寫完。
當他博士論文完成的時候,學校的同學及東京的學術界都感覺不可思議,一個中國人能在四年之內完成博士課程,並獲得博士學位,在日本尚無前例。立正大學的博士課程開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憑編號是第三號,這也是令日本佛學界驚歎的一件事。
日本之長,中國之短
聖嚴法師在日留學六年,一瓢一飯,生活備歷艱辛,但也是中國比丘在日本埋頭吸收彼邦學術、獲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極受國內外佛教及學界之仰歎。
他的博士論文,以研究智旭大師為中心而寫成的《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於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問世,中文版於一九八九年由關世謙中譯,臺北學生書局出版。
聖嚴法師在日本六年,深深地投入了佛法的海洋,當他在美濃時,讀遍佛家大經大論,建立佛家思想的骨架,在日本六年,則遍讀《大正》、《卍續》兩藏,除了重複的典籍略過,所有經論一概吸收化為自己乳血,因此乃能眼界為之大開,胸臆為之壯闊,然後再把自己的思想投回到中國佛學的土壤上。
根據聖嚴法師留學六年,從日本「取經」再運回中國佛域,再將這些精華溶入於著作之中,使我們對日本佛教真正的面目,有了一番清晰地認知。吾人眼前,現在透過法師東渡修學的鏡面,我們對日本佛教作如是觀:
日本佛教最大的成就在於,他們為佛法忘身的企圖心來建立佛教教育、文化、學術研究的方法與理念;一經參與佛教千萬年大計的學者、高僧、禪和子,無不與身家性命一併投入。
在中國人的眼裡,日本「有佛學而無佛教」,或「有真居士沒有真和尚」是有出入的。聖嚴法師透過六年的「和光同塵」生活,才驚異地發現,他們不僅有人修行,更有許多人嚴格在修行。
他們在明治維新時代之後,「蓄妻帶子」的家族傳承制度,卻是日本佛教得以延續的一項憑藉。除了「大本山」的專修道場之外,也有「隱居獨修」、「集體修」、「行腳修」的各種修行方式。
他們的「寺院」,是他們弘法的大本營、延續佛教的命脈,各宗各派的「大本山」及「本山」也創造了日本佛教的高等學府,培植了許多傑出的人才。
日本的佛學成就在於,方法學、語言學、梵文、巴利文原典的研究,及文獻學的開發與擴展,造成了日本今天的世界性學術地位;雖然日本沒有產生過東晉以後像道安、智顗、慧能這一類型的思想大師;他們只能夠解決早期文獻上的疑難,卻沒有解決義理的突破。
但是聖嚴法師還是從日本這塊佛教紮實的土壤獲得了現代中國所沒有的法乳滋養。
日本佛學者的敬業、勤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挖掘、精密的研究方法,以及鍥而不捨的樸實,值得我們讚美學習。
聖嚴法師不僅得到日本學者的素樸精神,也受日本佛學者的人格感召,與前輩對後生的無限慈愛與關懷,不厭其煩地諄諄善誘,愛生徒如己出,尤其對窮苦、努力的弟子,百般呵護。像坂本幸男教授,就是典型的日本良師。
禪在彼方,禪在此方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這位比丘學者,受到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之請,自東京赴美弘法,並在紐約大覺寺,以美國人為對象,開設「坐禪訓練班」。
在攻讀博士的繁忙生活中,聖嚴法師每日早晚的焚香拜佛常課仍未中輟。在東京,他所參訪過的道場,有曹洞宗派下的總持寺,隨原田祖岳禪師的弟子伴鐵牛老師學禪,在博士學位最後一年,有過三次禪七的經驗。足跡遍踏日本九州、本州東北部道場。他在禪七中也獲得日本禪師的印可,並贊成他去美洲弘揚禪法。
日本曹洞禪的特色:是「只管打坐」。「坐!坐!坐!」;把「念」放在坐的姿勢的正確、挺直;直到「雜念」漸漸消融。
日本臨濟禪的特色,是只參「無」字公案,滴水不漏,先從數息入手,俟妄心已息,再由「無」越到「公案」,直到你明心見性。
原田祖岳禪師是曹洞與臨濟禪的兩個系統傳承者。
聖嚴法師在從事學術研究之餘,不忘佛門本分事,當他在一九五○年以前,也留心過中國禪宗叢林,接觸到當代禪匠虛雲及來果禪師著作,對於唐宋中國禪師們的語錄,也曾做探索。
他到日本參訪道場,學禪、學教之際,才發現日本禪單純、形式化、千年不變;而中國禪則千變萬化,靈光閃忽;因此,學成之後,便決定採用本國的禪法來建立自己的禪道場,所以每次建立禪七,方法與機制都有所不同,這是中國禪的特色!
他一九七五年二月,獲得博士學位。為了接洽出版和校對論文,又在東京待了十個月。剛得到博士學位,他受到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的祝賀,於三月四日特假東京「六本木的隨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接著又收到了教育部、青輔會及救國團三個政府單位,聯合邀請出席「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的邀請函。於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回臺參加了會議的活動。
會議完畢,回到東京以後,辦理赴美的手續,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召開的第一屆佛教史學會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世界性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在會中,提出「中國近代史上的四位佛教思想家」的論文,同時也成為國際佛教研究會的創始會員之一。
一九七六年八月,美國佛教會在沈家楨先生的支持下舉辦一次松壇大法會,慶祝美國立國二百週年。
他和沈家楨居士分別在會場演講,這在美國是一種難得的盛況。同年九月,成為美國佛教會的董事、副會長、大覺寺住持。一九七八年底於美國成立「禪中心」,一九七九年七月將禪中心命名為「東初禪寺」,並剃度美國青年出家,出版英文《禪雜誌》季刊及《禪通訊》月刊,同年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並教授禪法。
仁為己任,任重道遠
聖嚴法師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出任大覺寺住持,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為止。在同年二月,則應臺灣中國文化學院邀聘,回臺擔任哲學研究所教授。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因剃度師父──東初上人(於先一年底)圓寂,由東公遺囑指定為「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繼承人,並晉任為該館館長,十月九日應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
這一年,聖嚴法師是四十八歲,也從這一年開始,他在臺、美兩地輪流主持三個道場,和一個「佛學研究所」。在臺灣未曾見到像聖嚴法師在「北投農禪寺」模式──以文化人為中心的寒暑兩波段的禪修活動,也沒有見到中國式寺廟佛學院會升格為學院式研究教學場所。
在「定慧雙修」上,是中國比丘僧在承擔「佛教行解」兩端兼顧教育、負起「昇華」責任的第一人。佛教的歷史包袱太重,聖嚴法師的文化使命,將使他成為宗教兼顧發展佛教學術的推動人。「佛教」能不能由於他的實踐其文化使命而再生新枝,這都在他的深弘大願裡成為盡形壽奮鬥的目標。
美國的道場──禪中心(東初禪寺)最初設在紐約皇后區,柯羅娜街三十一號。過了五年之後(一九八二年)由於不敷使用,轉到同一條街的五十六號,到今天以西方的佛寺標準而言,已具規模。
這座道場,佔地面積五千平方英呎,建築面積為九千一百平方英呎,分別設為停車場、禪堂、講堂、寮房、圖書室、會客室,它是財團法人組織。起初,聖嚴法師原意為英語人士為對象來弘揚「中國禪」,可是現在中國人卻超過了美國人。這個道場平時是雙語教學,「小參」則是以英語交談。這一道場,也成為中國法師引用雙語傳道的第一人。
這裡與臺北的農禪寺,每六個月分別訂有「行事曆」,「行事曆」決定了聖嚴法師什麼時候在紐約,什麼時候又到了臺北。「行事曆」決定了「中西」兩個道場文化與禪修的實際內容。
紐約平時有常住五人,其中兩位青年比丘,兩位待落髮的女眾。平時參與活動的「中美」人士,經常是五十到一百人。此間所創辦的英文《禪通訊》月訊及《禪雜誌》季刊,發行到世界各地約二千多份,寄發地區有二十五個國家。在紐約創立的法鼓出版社,已為聖嚴法師出版了六種英文的禪學著作,也行銷世界各國。
東初禪寺,在紐約地區已算重點道場,它的活動頻率、信徒人數,以及中英文報紙見報率,已成為世界各地佛教的重點新聞。

▲一九七六年聖嚴法師於美國紐約大覺寺擔任住持並開設禪坐班與十位學生攝於該寺觀音殿。
在臺北,農禪寺從一九七八年,聖嚴法師接承文化館之時,經過一番策畫,到一九七九年開始對外開放設立「禪道場」,由聖嚴法師親自主持,並且接受中國知識青年剃度以及社會知識分子定期打坐、參禪,以及對內對外的演講弘法活動。迄今在農禪寺學習禪坐的人數及接受了三皈依的信眾,已超過四萬及五萬二千多位,該寺出版的《人生》月刊及《法鼓雜誌》,發行數量合計已超過十二萬。聖嚴法師一身而兼有東西兩個道場的弘法大任,真可謂席不暇煖,以佛教興滅為己任了。
可是為了對佛教「從根救起」,捨高級教育之人才培養之外,別無他途。當一九八一年已改為大學的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正式成為教育機構,七月底招收第一屆碩士班學生八名。同年六月聖嚴法師受聘為中國文化大學的華岡教授。到一九八四年,文化大學佛研所因為受到學校當局政策性影響而停辦,於是聖嚴法師在一九八五年假北投「佛教文化館」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招收大專畢業學生,授以三年學術訓練,再做重點培養出國深造,修讀博士學位,到一九八七年獲得教育部核准立案,所址移入「佛教文化館」重建後的新址,正式負擔起「培養高級佛教學術人才與悲智雙修的弘法人才」的重任。
「中華佛學研究所」到一九九五年的夏天已十四度招生,它的教學特色,除聘請國內外佛學著名師資教學,課程與一般碩士研究所應修的相同之外,重點在「巴、梵、藏」文的學習,以利原典的研究,並藉這一途徑與國際佛教學術界互相溝通。
在作風上,採開放教學制,除本所學生之外,凡有國際著名教授來所開設中短期講座,一律邀約。
在學術交流活動上,一九九○年元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在臺北中央圖書館由聖嚴法師主持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網羅世界一百四十位學者參與,又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假臺北圓山飯店主辦了「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與會學者一百五十餘位,這兩次會議將臺灣佛學研究氣氛,帶到最高峯。

▲一九九○年元月由聖嚴法師主持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邀請了世界各地一百四十位學者參與,將臺灣佛學學術研究風氣,帶到最高峯。
在重要目標上,除培養高級學術弘法人才,也兼及訓練「管理」人才、修道及弘法專才。務必做到「解行並重」、「定慧兼修」。到一九九六年為止,在東西兩半球依止聖嚴法師出家修行的男女弟子,已超過了八十位。
聖嚴法師本身是「修道」與「學術」兼重,他深以為沒有「行持」的基礎,研究學術者,則與佛法無法相應;終致學術歸學術、佛法歸佛法的內在歧異現象,他要的是既要有學養,又要有道行的承傳弟子。
他對日本佛學者「行解雙運」十分敬佩,日本有很多學者,淡泊一生,不是參禪便是念佛;像鎌田茂雄教授修禪、水谷幸正教授念佛,他們卻有相當深厚的根基,極為崇高的宗教情操。
同時,被誤認為日本佛道場與佛教徒都飲酒肉食的印象,日本人有不同的文化認知,但真正的修道者是不肉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聖嚴法師的理想中國佛教與佛教比丘僧,是兼具日本佛教人的謹嚴、學養、宗教情操與中國比丘僧的持清淨戒律與重視有道高僧的人格模式。只有具備這種道德素質的佛教人才,才是復興中國佛教的最大寄望!
淘金琢玉,造就龍象
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以前,「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優秀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已有十一位,分別有在日本東京大學獲得文學博士的惠敏法師、鄧克銘居士、同校博士班的厚觀法師、名古屋大學博士班的郭瓊瑤居士、九州大學博士班的陳宗元居士、京都大學碩士班的果賾法師、京都龍谷大學的開智法師;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修畢博士課程的梅迺文居士、密西根大學交換研究員的果祥法師、夏威夷大學碩士班的李美煌居士、佛羅里達大學碩士班的陳秀蘭居士。
歷屆留在國內的畢業研究生,已有數位留在本所教授初級佛典語文,分別有教授初級藏文賴隆彥及曾德明居士、教授初級梵文的宗玉媺居士、教授佛學英文的杜正民居士。另有數位在各佛學院及高職學校教授佛學課程,為臺灣的佛教教育帶來一批優秀的師資及弘化人才。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起學成返國的惠敏法師、鄧克銘居士,各方爭相延聘。惠敏法師目前是西蓮淨苑副住持,並在中華佛研所、法光佛研所、國立藝術學院擔任教職。鄧克銘居士目前是「華嚴法律事務所」的負責人,也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專任副研究員。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七日中華佛學研究所與國際上知名的學術機構日本駒澤大學締結學術交流合約,建立了合作關係。
中華佛學研究所與國際上知名的學術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目前已有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學、東京的立正大學及駒澤大學;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密西根大學;泰國的法身基金會。為提昇中國佛學的學術地位,貢獻頗多。
中華佛學研究所從創立時篳路藍縷、搖搖欲墜的困境中,到今日的開花結果、穩定成長的局面,不僅促使臺灣佛教界開始重視佛學研究及高等佛教教育,也為中國佛教造就一批法門龍象,為中國佛教的發揚光大奠定了初基。這一切都憑藉著聖嚴法師堅定的意志力及推廣佛教教育的大願力。
悲智雙運,寰宇弘法
一位中國比丘僧的身影,自一九七六年以來經常於夏冬之際,遊化於歐美各國五十座著名學府之間,主講超過百餘場有關中國禪宗及佛教的精闢演講。聖嚴法師在美洲大陸弘揚中國禪法及正信佛教,其艱辛的情況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法師除了堅毅面對困境之外,更積極地講經說法、弘揚佛教,弘法地區也遍及加拿大、英國、哥斯大黎加、香港、捷克等國家。
在臺灣,二十年前的大學校園,出家僧尼是不准進去的,不僅不准弘法,連穿僧裝讀書都會受到排斥。而今各大學能夠尊重宗教的自由,允許大學佛學社團邀請法師至大學校區演講。聖嚴法師歷年在國內期間,經常應邀到各大學做過許多場的佛學講座,並舉辦佛學課程充實的「大專佛學夏令營」。法師希望能藉此開拓學佛青年的視野,使其瞭解到要深入佛法或發揚佛教,須先重視佛教教育及佛學學術研究。
法師所著近六十本的佛學及禪學著作,曾影響並扭轉當代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信仰佛教就是迷信的傳統看法,並進而學習佛法及參禪。而其著作中的八本英文禪學著作,也接引許多異國人士瞭解中國禪宗的思想及修行法門。
聖嚴法師不僅在學術領域上,引導臺灣佛教界能從佛教歷史、經論及近代佛學研究作品中,瞭解佛陀的本懷及認識真正的佛法。他也在臺灣、美國、英國等地,迄一九九六年為止,主持了近一三○期的禪七,並在法鼓山舉辦了十屆的「社會菁英禪修營」,指導許多中外人士進入禪宗修行的領域。法師在佛教教理及修行實證兩方面均能兼顧並加以弘揚,使信眾能走向「教證合一」的理想境界,他認為唯有教證兼弘,佛教才能真正的發揚光大及源遠流長。
一九五六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每年一次冬令救濟活動。一九七八年聖嚴法師晉任該館館長後,繼續擴大辦理,救濟更多的貧苦人士。透過冬令慰問的救濟活動,聖嚴法師以佛法開示及佛書結緣,令受濟者在物質及精神雙方面,均能蒙受利益及法益。法師並經常將十方檀越善心布施的財物,捐贈給榮民總醫院惠眾基金會、智障團體、養老院、育幼院、聾啞福利協進會、流浪動物之家、野鳥協會、臺北木柵動物園建野生鳥類復健鳥籠等二十餘所慈善公益團體。
聖嚴法師多年來在佛教教育文化及社會慈善救濟的表現,已受到政府當局與社會大眾的肯定及讚揚,並於一九九○年榮獲內政部頒發「好人好事八德獎」、一九九二年臺北市政府頒發「市民榮譽紀念章」、一九九三年吳尊賢基金會頒發「吳尊賢愛心獎」及傑出社會運動領袖獎、一九九五年獲社會教育有功貢獻獎、一九九六年獲頒國際傑人獎。內政部及臺北市等也經常頒給感謝狀讚揚法師的善行義舉。
導正佛法,建設淨土
在多元化的社會下,佛教也出現多元且新的狀態,此時有能力、有抱負、且具號召力的法師或居士均可發揮其影響力,而形成新興的佛教團體。表面上,這些新興團體號召許多人對佛教產生信心甚至成為佛教徒。但是在多元化的發展之下,由於彼此的觀念不同,極易產生教內衝突矛盾及教義混淆不清,並使廣大的佛教徒產生迷惘。
聖嚴法師以年近不惑之身,遠赴日本留學,目的就是要從日本百餘年來,對佛教歷史、經論等的豐碩研究成果中,吸取經驗並學習其成就,能夠對衰微已久的中國佛教有振衰起弊之作用。法師以慈悲的宗教胸懷與紮實的學術素養結合,希望能引導大家從基本的佛教理念去尋找源頭,也是回歸佛陀化世的本懷。
今日世界的政治紛爭、戰亂頻仍、生態嚴重破壞都是因為人類自己的行為,造成危害人類本身未來生存的危機產生,而人的行為乃源於人心,而佛教最重視就是人心問題的探究和解決。若是能透過教育以佛法來教化每個人的心,也就是解決一切問題源頭。
為將佛陀教法落實在人間,為使我們這個時代社會,因正信的佛教而帶來光明幸福。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而達成這個理念的方法是「推動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法師認為佛教教育是發揚佛法的必要先決條件,而今日佛教教育更需要具備系統化、全面化及層次分明的教育機構,才能符合現在及未來時代發展的需要。
自一九八九年起,聖嚴法師與認同法師理念的護持居士們,選定臺北縣金山鄉面對北方海洋的山坡地約六十甲,定名為「法鼓山」。希望以此地作為推動全面佛教教育的根據地,以便達成「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法鼓山的建設共分為三期:
第一期工程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遷建工程,中華佛學研究所在今日佛教教育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它兼具發揚中華文化,推動中國佛學研究,培養佛教學術研究暨弘法人才功能和目標。第二期中程目標是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建校工程。第三期遠程目標是世界佛教文教及修養中心。
「法鼓山」的建設計畫,是聖嚴法師以整個世界佛教為己任的遠圖之基礎,「法鼓山」建設計畫之推動仍有待十方的檀越大德,能發「捨無量心」,共襄歷史的盛業。
聖嚴法師希望促成「世界一家」的佛教早日完成,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佛教徒能夠不分宗派、不分區域、不分種族共同融匯為一種「正知正見」的世界佛教。他也寄望於「法鼓山」能帶動臺灣的佛教界,乃至全世界的佛教,走上佛教現代化之路。法鼓山將以佛教教育帶動社會文化的提昇,經由文化的提昇來改變眾生心靈,以達成人間淨土之推廣實現。
一代宗師,為法盡瘁
聖嚴法師一生致力於弘揚人間佛教,推動全面佛教教育,盡心盡力地推行正信佛法於世界各地。長久以來法師心中一直覺得遺憾的是:「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卻那麼的少。」
法師希望讓更多的人認識佛法,而這個希望需要更多的弘法人才一起推動。然而弘法人才的培育,需要完善的佛教教育制度與環境。環視當時國內對佛教教育的漠視,法師深切體認到「今天不辦教育,佛教沒有明天」,因此為提昇國內佛教教育水準及培養弘法人才,他發願以其瘦弱的身軀及畢生之生命來努力完成之。
聖嚴法師於一九六九年束裝遠赴日本留學,學成之後即奔波於臺、美兩地巡迴演講佛法、指導禪修,並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培養更多佛教人才。這一切的努力辛勞,都是為了把「這麼好的佛法」,弘揚到世界每個角落,屆時我們的世界也將成為真正的人間淨土。
聖嚴法師的努力漸獲社會大眾的肯定及景仰,尤其佛教四眾之敬愛,他的學術成就固是一端,而最大的因素,則是他能依照佛律,重新剃度,正式受戒,洗卻舊容,堅持佛戒的所致。
聖嚴法師是出入僧俗一面光潔的明鏡,一位光明磊落的比丘僧,一位將在歷史舞臺佔有重要地位的宗教家,而他獻身推動國內佛教教育百年大業,也將為中國佛教寫下歷史的新頁。
這位謙誠而深具智慧的一代宗師,為弘揚佛法已奉獻其全部身命而沒有個人的事業。曾有一位美籍神父,見到簡陋的美國東初禪寺時問聖嚴法師:「如此清苦,目的何在?」法師的回答是:「不為什麼,只為使需要佛法的人,獲得佛法的利益。」
聖嚴法師如今雖已受到國內外廣大信佛學佛人士的尊敬,而認同他所推行「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理念的人士,也越來越多,但他經常謙稱:「我什麼也沒有做,所有的奉獻,都不是我的,我只是一根輸血的導管,把志願捐血者的血液,經過導管,輸給需要血液救命的人。」
聖嚴法師也常對弟子們說,他是一個普通人,只是因為發覺佛法對自己是如此的有用,想必對人類社會也能產生作用,所以努力修學佛法及弘揚佛法。由於跟隨及護持的僧俗弟子漸漸多了,大家廣為宣傳及讚揚,才將他襯托成為一位高僧。但是法鼓山的形象及其對於社會的貢獻,應歸功於每一位熱心參與及認同關懷的大眾。法師為報答佛教的深恩及感謝大眾的護持,將會夙夜匪懈,為法獻身,盡勞盡瘁。(本文為陳慧劍居士定稿於一九九○年九月一日,一九九三年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修訂部分內容,已取得原作者之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