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將軍
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我隨著一個電臺,配屬到高雄要塞,就是住在現今的壽山公園裡,當時的公園,漫山是雜草,以及成叢的相思樹,沒有開放遊覽,也不像一座公園。但我住在那裡,卻是很大的方便,常常去市立圖書館,一坐就是半天,看不完的書,可以借出來,看完了,再去換。因此,我自那時到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止,在哲學、宗教、歷史、文學方面的書,看得很多,並且做了好多筆記。其中以文學作品看得最多,幾乎在當時所能借到或租到的中外名著的中文本,我都找來看了;同時費了一股子傻勁,為那些著作寫心得,編入名錄,分析書中人物的性格特點,注意作者表達人物的技巧。另一方面,我也勤奮地學著所謂小說的「創作」。
我寫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自以為是新詩的詩,用幾個筆名,投向各處發表。到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我能於《佛教青年》上發表〈文學與佛教文學〉,並引起教內一時的爭論,那也要歸功於此一時期對文學、對寫作的研究。只以我的技巧尚未成熟,文藝的思想也未通透,所以,既未因此成名,更未因此成功。那時,我自己買了一張竹製的書桌,絕大部分的時間,便消磨在那書桌上。
我有幾位同學,也很用功,多數是為軍事教育的深造用功,用功的重點,很多是在英文,他們希望有機會去美國受訓,所以常往教堂裡跑,聽英語講道。另有一些則是為高普考而用功,用功的重點是在社會科學。他們見我用功的方向,不倫不類:看佛經、看文學、看哲學,又看宗教,所以好心的勸我,教我認定一個目標。其實我是有目標的,我既不想以軍人為終身的職業,也不想到行政機關討一碗飯吃,我是藉此機會打一打文學的基礎,然後再專志於宗教哲學中去,因為我的宗旨,很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仍做一個出家人。憑良心說,我之能夠塗鴉寫文學,主要是在軍中磨鍊出來的。
到了鳳山之後,我常去煮雲法師的佛教蓮社,在他那裡,我可借到一部分的佛書,並向他請教一些佛學的問題。那時的煮雲法師,已在全臺灣聞名了,他經常環島佈教,我說他是一座活動的佈教所。同時,在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間,他又出了一本《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的演講錄,轟動一時。至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基督教有個叫作吳恩溥的牧師,出了一冊《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當我看了煮雲法師及吳恩溥牧師的兩書之後,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冊《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於是,僅以十來天的時間,寫成了五萬餘字,交由煮雲法師出版。這是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八月下旬的事。
正在這時,我也為著調換工作單位而忙。那是由於友人的介紹,考取了國防部的一個機關。至九月二十五日,我便奉准調到新店去了。
因為新店離臺北市很近,我與臺北佛教界的接觸,也就容易得多了。
自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開始,我為好幾家佛教刊物寫文章了。最先是因性如法師接編《人生》月刊,他知道我會寫文章,所以硬是逼著要稿,他對我一向也是不錯的,礙於情面,我就寫了,並且我也從此有了一個「醒世將軍」的筆名,這不是因了軍人的身分而取,乃是為攝化眾生與喚醒世人而取,這個筆名,一直用到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冬天第二次出家後,才停止使用。另外我從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元旦開始,同時用了一個「張本」的筆名,在《海潮音》及《今日佛教》上寫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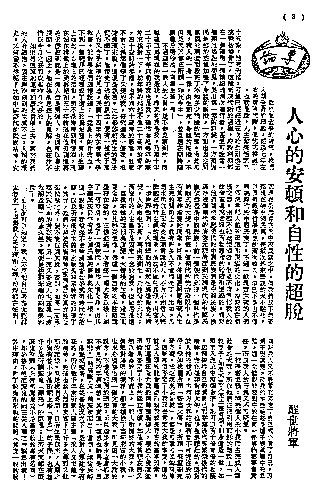
▲為攝化眾生、喚醒世人,作者以「醒世將軍」之筆名在《人生》月刊上發表文章。
佛刊很多,為《人生》寫開了頭,其他幾家,也向我索稿。因此,我就放棄文學的習作,專寫佛學性的文章了。
寫文章的路子一開,思想一通,理境一現之後,便會源源不絕地一直寫下去,寫了一篇又有一篇,路線雖只一條,境界卻是越開越寬了,又像滾雪球似地,知識一天天地增進,文思也一天天地廣闊,不論看什麼書,不論吸收何種知識,均會匯集到我所歸宗的中心思想上去,漸漸融合,慢慢凝聚。做學問做到此一地步,真是一大樂事。但此在我,到了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才開始活潑起來的,雖然那也只是我在學問之門中見到了一線曙光,在思想之海中嘗到一滴之味而已。但是好多人以為我是開悟了。
有時候思潮澎湃,不能自制,即於抱病之際,也要執筆一吐。我在新店時的工作很苦。而且常常通夜工作,我不慣夜間生活,夜間工作之後的第二天日間,並不能夠將晝作夜,補足夜間的睡眠,故而每於夜間工作之後,次日又於白天讀書、寫文章。

